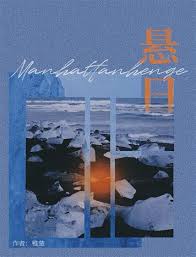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我真沒想和大佬協議結婚》 19
因為堵車,那輛邁赫在車流中一不,即便是在豪車遍布的商業街也顯得尊貴無比。
更讓喬瑜欣喜的是,認識這輛車。
今天下午從盛嘉總部出來時,遠遠地看到過車牌號,囂張的一串連號,車是誰,不言而喻。
如果不是勢人,喬瑜必然不會選擇去敲開陸嘉延的車窗。
但要穿著十幾公分的高跟鞋在商業街這個人人悶死人的地方站三四個小時,寧愿鋌而走險去搭陸嘉延的車!
喬瑜鼓足了勇氣,敲了敲車窗。
幾秒之后,車窗落下,后座果然是陸嘉延那張俊的臉,即便是下午才見過,如今再見到,依舊讓喬瑜恍惚了一刻。
“陸總,不好意思打擾您了。外面雨大,我打不到車,方便的話能麻煩你送我一程嗎?”
陸嘉延的神態看上去與下午并沒有什麼區別,帶著淡淡的疏離。
喬瑜在等待的過程中,忽然有點后悔自己做的這個沖的決定。
哪兒來的自信,覺得陸嘉延會看在外面暴雨的份上,讓上車?
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喬瑜以為自己要被拒絕時,陸嘉延打開了車門。
聽見自己的心跳聲重重地加速了一下,說了一聲“謝謝”之后,接著便提著擺小心翼翼了上了車。
直到落座之后,喬瑜都不敢相信自己真的搭上了陸嘉延的車。
對方似乎有點不太舒服,一直沒什麼表的沉默著,間或著眉心。
喬瑜大氣不敢出,在聊天框里跟弟弟喬言瘋狂打著嘆號。
把自己搭到了陸嘉延車的事從頭到尾復述了一遍。
喬言:【?】
【姐,什麼霸總小言的開端?你該不會是墜河了吧?】
Advertisement
喬瑜:【……】
【人家有老婆。】
喬瑜懶得理喬言的胡言語,大概是弟當明星演多了什麼霸總言劇,把現實生活也當了偶像劇。
只不過視線停留在喬言的最后一行字上面,不免也有些心。
畢竟陸嘉延居然真的讓上車了……雖然剛才的行為,已經接近于道德迫,那麼大的雨,陸嘉延總不能真的讓在雨中一直站著。
只是,喬瑜依舊忍不住發散思維,那是不是說明他對自己還是有點印象的?
正當胡思想的時候,陸嘉延冷淡地聲音響起:“喬小姐,你有錄音筆嗎。”
做采訪工作的,包里基本都常備著幾只錄音筆。
但不知道陸嘉延這時候問起錄音筆是什麼原因。
喬瑜點了點頭,將錄音筆拿出來:“陸總,您是要用錄音筆?”
陸嘉延沒什麼表點頭,指了指筆:“方便打開嗎。”
喬瑜:?
陸嘉延慢條斯理道:“從現在開始,請保持錄音筆打開的狀態,不要關閉。”
他了下眉心,朝副駕駛的姚深位置微微仰頭:“姚深。每隔十分鐘給二匯報一下路況。”
這一刻,陸嘉延忽然想起了盛明稚那副驕縱又任的脾氣。
要是被這個小祖宗知道他大半夜的送別的人回家,就是沒事兒也能被他作點事出來。
為了以防萬一,他哂笑一聲,補充道:
“記得發定位給他。”
一旁的喬瑜已經被這一通作驚呆了。
甚至都沒有反應過來陸嘉延在和說話。
“抱歉。”男人的聲音依舊溫潤,但喬瑜卻到了一涼意。
仿佛剛才從大雨中出來,敲開陸嘉延車窗心的那一點無法見的小心思,已經完全被男人看穿。
Advertisement
陸嘉延的音甚至比窗外的雨水還要清冷:“我人查崗查的嚴,希你不要介意。”
-
盛明稚剛從錄制棚出來,手機就一連收到了十條消息。
都是姚深給他發過來的定位,十分鐘一條,還盡職盡責地播報了陸嘉延的行程。
盛明稚:?
想也知道不會是姚深主發神經,多半是陸嘉延授意的。
【他有病?】
盛明稚無語:【定位發給我干什麼?找不到路麻煩他去高德,除非他現在出車禍需要我親自去醫院現場簽名自愿放棄手,否則我對你老板的行程沒有興趣(黃豆微笑)】
大爺這幾天還沒消氣,姚深的作無疑加劇了他的怒火。
發完這條消息,盛明稚就直接連坐,把姚深也給拉黑了。
-
剛說完人查崗嚴就瞬間被打臉。
陸嘉延從姚深得知對方也被拉黑之后,頓了下。
接著面不改,神淡定地開口:“你看。我就說他會吃醋。”
一副還好我有先見之明的自大狂妄。
姚深:……
那個,老板,我覺得二可能,不是在吃醋?
還有,現在我們倆都被二拉黑了,您想過接下來怎麼聯系二嗎?
作為下屬,老板的事就是他的事。
老板的私事同理,畢竟每次小公子跟陸總吵架,倒霉的都是他們這些領工資的。
姚深艱難地開口,準備提醒一下陸嘉延認清事實:“陸總,有句話我不知道當講不當講……”
陸嘉延挑眉,斜著瞥了姚深一眼,威脅十足,冷颼颼地:“對著你的年終獎講。”
姚深:……
我又覺得沒什麼好講的了!
邁赫緩緩開進西山壹號的地下車庫,紅酒的后勁上來,陸嘉延微醺的覺略微強烈些。
Advertisement
姚深將他送到了客廳才走,走之前順便十分的把錄音筆放在了茶幾上。
不間斷錄音了一小時,每隔幾分鐘都伴隨著姚深隆重的語音播報。
可以說是當代賽博男德的另類現方式。
陸嘉延懶散的倚在沙發上,視線落到了窗外。
傾盆大雨還在繼續,或許是喝了點酒的緣故,陸嘉延今晚想起盛明稚的次數格外的頻繁。
頻繁到甚至讓他自己都覺到意外。
他記得,第一次見到盛明稚,也是這樣的大雨天。
盛明稚那時候只有十二歲,但格遠遠比其他同齡的孩子瘦弱。他像是一個不會說話的瓷娃娃,漂亮的不像男孩,沉默又向。
只有那雙小狐貍一般靈的雙眼,過來的時候,著他心底的緒。
當“沉默”和“向”兩個詞從陸嘉延的記憶中浮現出來時,他自己都被逗笑了。
現在盛明稚這小祖宗哪兒還跟這兩個詞靠邊,不知道中間那幾年不見,他去什麼地方進修了一脾氣,驕縱跋扈的很有水平,活潑的過了頭。
那天小盛老師的萬人演唱會表演又冷不丁的闖陸嘉延的腦海中。
原本沒有開燈的客廳安靜且孤寂,現在卻響起了陸嘉延低低的悶笑聲。
或許,他一直對盛明稚有點兒誤解?
三年不見,他似乎比他想象中的更加有趣。
-
盛明稚回到家中,看到的就是這麼一幕。
陸嘉延半倚在沙發上,不知道是不是睡過去了,一點靜都沒有。
一周沒見,盛明稚也沒想到回來就看到了自己這位便宜老公。
客廳里安靜的令人發指,盛明稚靈敏的嗅覺聞到了空氣中一酒味。
Advertisement
他還奇怪陸嘉延對自己一言一行這麼嚴苛的男人,怎麼會在沙發上就睡著了。
原來是喝了酒。
盛明稚嘀咕了一句難聞死了,就想甩了陸嘉延顧自己上樓。
但窗外“轟隆”一聲雷響,閃電落下,空氣中的冷意傳來,勾住了盛明稚的腳步。
十一月降溫的快,西山壹號別墅雖然是恒溫的,但在沙發上晾一晚肯定冒。
盛明稚還是心了一瞬,默默念叨是為了讓狗男人有更好的去賺錢讓后養他,為了自己長久的榮華富貴,他才勉強扶陸嘉延回房間的。
只是剛蹲下,盛明稚的視線就不由自主的落在陸嘉延的臉上。
暖黃的燈下,男人的皮致到離得這麼近都看不出任何瑕疵,鼻梁高,廓深刻,睫也長的不可思議,落在臉頰上有一片扇形的影。
猜你喜歡
-
完結194 章

變成人魚被養了
擁有水系異能的安謹,穿越到星際,成了條被拍賣的人魚。 斯奧星的人魚兇殘,但歌聲能夠治療精神暴動。 深受精神力暴動痛苦的斯奧星人,做夢都想飼養一條人魚。 即便人魚智商很低,需要花費很多心思去教育培養。 斯奧星人對人魚百般寵愛,只求聽到人魚的歌聲,且不被一爪子拍死。 被精神暴動折磨多年的諾曼陛下,再也忍不住,拍下了變成人魚的安謹。 最初計劃:隨便花點心思養養,獲得好感聽歌,治療精神暴動。 後來:搜羅全星際的好東西做禮物,寶貝,還想要什麼? 某一天,帝國公眾頻道直播陛下日常。 安謹入鏡,全網癱瘓。 #陛下家的人魚智商超高! #好軟的人魚,想要! #@陛下,人魚賣嗎?說個價! 不久後,諾曼陛下抱著美麗的人魚少年,當眾宣布。 “正式介紹一下,我的伴侶,安謹。” 安謹瞪圓眼睛:?我不是你的人魚主子嗎? 溫潤絕美人魚受v佔有欲超強醋罈子陛下攻
42.6萬字8 8679 -
完結239 章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41611 -
完結135 章

當軟萌受嫁給暴躁總裁
冷酷不耐煩後真香攻×軟萌笨蛋可憐受 1. 江淮從小就比別人笨一點,是別人口中的小傻子。 他這個小傻子,前世被家族聯姻給了一個人渣,婚後兩年被折磨至死。 重活一次,再次面對聯姻的選項,他選擇了看上去還行的“那個人”。 在同居第一天,他就後悔了。 2. “那個人”位高權重,誰都不敢得罪,要命的是,他脾氣暴躁。 住進那人家中第一天,他打碎了那個人珍藏的花瓶。 那個人冷眼旁觀,“摔得好,瓶子是八二年的,您這邊是現金還是支付寶?” 同居半個月,那個人發燒,他擅自解開了那個人的衣襟散熱。 那個人冷冷瞧他,“怎麼不脫你自己的?” 終於結婚後的半年……他攢夠了錢,想離婚。 那個人漫不經心道:“好啊。” “敢踏出這個家門一步,明天我就把你養的小花小草掐死。” 3. 後來,曾經為求自保,把江淮給獻祭的江家人發現——江淮被養的白白胖胖,而江家日漸衰落。 想接江淮回來,“那個人”居高臨下,目光陰翳。 “誰敢把主意打他身上,我要他的命。” 4. 江淮離婚無門,只能按捺住等待時機。 與此同時,他發現,自己的肚子竟然大了起來。 那人哄反胃的他吃飯:老公餵好不好? #老婆真香# #離婚是不可能離婚的,死都不離# 【閱讀指南】:攻受雙初戀。 【高亮】:每當一條抬槓的評論產生,就會有一隻作者君抑鬱一次,發言前淺淺控制一下吧~
28.5萬字8 13197 -
完結115 章

咸魚少爺穿成反派的白月光
唐煜穿書前住的是莊園城堡,家里傭人無數,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錢多到花不完的咸魚生活。一覺醒來,唐煜成了小說里的廢物花瓶,母親留下的公司被舅舅霸占,每個月克扣他的生活費,還在男主和舅舅的哄騙下把自己賣給了大反派秦時律。他仗著自己是秦時律的白…
39.1萬字8 99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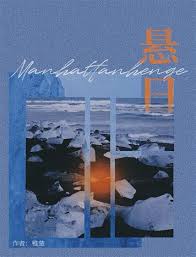
懸日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衝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後悔。 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 -“至少在第42街的天橋,一無所有的我們曾擁有懸日,哪怕只有15分20秒。”
47.2萬字8.18 161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