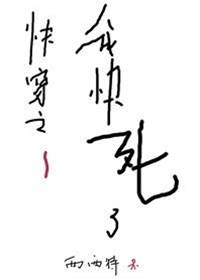《典獄司》第7章
第八章張啟山
深深的疲倦,眼球的刺痛,酸脹。口的濁氣總是積著,怎麼呼氣都歎不出去。
得好生歇息上幾日,子快垮了。
算算多久未去監獄了?一周?兩周?唉……二月紅。
椅子周圍一地煙灰,怕是能踩腳印出來。近來多夢,卻總是記不住容。濃茶不住倦意,倒是羨慕起來監獄裡那位來了,一次能睡個夠
也不知他燒退了沒有,上一次走時正在發燒。一夜二人就裹一件大氅睡,早上醒來發現整個人蜷團在我後,凍得青紫。一句話都不說,若是推推我讓我醒來,也不至於落個高燒不退的結果。
要說對他到底是個什麼,這些日子也細細碎碎的想了不。越是越是顯出平靜的彌足珍貴,高發狂的日子,卻想監獄裡至一片平淡,總有個人兒,非他願也好,被迫也好,死死的等著我。不知還會不會睡著在門口的太師椅上?一臉,連眼睫都是一扇,就那樣安安靜靜的抱著我的服昏睡。
這日子過的比衝前線還張,比如有理不完的戰報,和總是逾期的軍餉。
前幾日為了軍餉還下了一次鬥,四萬人的隊伍調走兩萬去一線,剩下的中央不予發餉,只得各自想辦法。剿匪的上山,買糧的北上去蒙古,俄國,數來我這下地還算最輕鬆的,只是近來神不佳,前前後後進斗幾次,險些折了進去。沒了那花左右照應,大意了不。。
若是他日戰死,想來他二月紅不會獨活。出監獄唯一的可能就是來陪葬,生死由我,不看他。
何時能再待到他傾出點?那日帶那兔子去試探,現在想來萬分後悔,其實我只是……只是想看看他的反應。哪怕是只喊一聲「張啟山!」,我就停下來,抱著他告訴他,這都是我的不對,再也不會了。
Advertisement
實則……也是二月紅的子——骨子裡的東西,是嗎啡或任何刺激都不能磨滅的——就那樣怔怔的看著我,我以為他會說些什麼,我焦急的期待他的阻止,不料他卻別過頭,閉了眼,將那殘戲一段一段唱了個乾淨。
下山尋一個哥哥,憑他打我,罵我,說我,笑我。一心不願佛,不念彌陀般若波羅。
也不能全算酒作怪,不得不說那場□般的□確實是一直積下的暴怒緒。至在當時我以為他會有些許反應,譬如憤怒,難過,甚至掉眼淚……結果他就那樣的看著我,簡直就像是在看一個死人,瞳孔的都淡了。甚至厭惡的別過頭,一眼都不願多看!生怕污了眼。
那些日的怕是再不會有了。想他那晚是拖著被□,難過到死的子,生生哭著爬起來狠狠摔了我送的簪子,折半或是碎,我不知道,只知道不值,或者在他眼裡什麼都不值了,早已。
我去看看醫生,再配些安神的藥來,自從離了他以後再沒睡個一個好覺。
在醫生的診所裡,看他那道貌岸然的樣子。下的胡茬,看他瘋狗般的忙前忙後,一副馬上就快累死的模樣,實則是刺激太多,大腦過度的疲勞了。給他的刺激,就像二月紅如我,缺失便無法正常生活。
「聽說鴿子和硃砂,能用來紋?」我問道。
「能。只是效果不大明顯,況且又是大紅,很有人紋。倒是有不歡館的人喜歡。」他答道,並不停下手中的活兒。。
我拿起硃砂瓶子把玩,疑問道:「歡館?」
「紋著平時又看不出來,但凡緒波,喝酒,□,這東西就顯出來了。又是大紅的,自然歡館喜歡。」。
Advertisement
「呸,別一口一個歡館的。」我打開瓶蓋倒了一點點末,歡館二字不知為何格外刺耳。
他在給人手,來他這的醫治的不是特務就是政治犯,份敏,我倒不怕這些,關鍵在於他並不介意我在旁觀看。。
「還有臉說歡館不對了?上回那兔子哪去了?」他摘了口罩,淋淋的手拿了我手裡的硃砂瓶子,又說道:「好硃砂金貴著呢,哪兒能容得了你這麼使喚。
我挑眉看他,噗嗤笑出聲來。起奪回瓶子,整罐倒在那在病床上躺著的人上。
「兔子被我置回去了。」我抖抖瓶子,把瓶底兒裡硃砂倒乾淨,然後「」的砸在他面前:「找些比這個更好的來,我要用。」
他回頭看看仍在麻醉中渾然不覺的病人,說道:「上頭問起來可要幫我頂著,我可不願被說醫不。」手又說道:「這人怕是活不了。」
「干我何事?」我笑,他也笑。本就是那不該茍活的貨,來世好好做個人,因為賣國賊只能算個貨。
再次見到二月紅,沒有我預想到的面如死灰,或是置我不理的狀況,當下心便好了很多。我抱著他,看樣子不燒了,鼻尖埋進他的長髮裡,深深的吸口氣,口而出:
「甚是想念。」
他一,推開我,低下頭長髮又遮了眉眼。
我手挑起他眼前的頭髮,說道:「了服。」
蒼白的臉一下困窘起來,用大拇指腹磨磨他那小臉:「自己,不想給你難堪。」
醫生隨我一同前來,畢竟紋這種技活還是需要指導的。
他泡在木桶裡,抬著頭著天花板,長頭髮垂在木桶外。木桶不夠大,我只能幹看著熱氣將他那小臉騰出一層紅暈,細細的汗。
Advertisement
「一會給你紋,提前道一聲。」我倚著門站著,他嘩啦一下回過頭,一不的看著我。
許久沒發洩過了,我實在怕忍不住。他還需要力做紋,想到這裡我便轉了,點了煙出去和醫生討論圖案規劃。。
天火紅蓮。這文縐縐的名字已經被醫生嘲笑過了,而從心論,我倒覺得真的很好聽。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一個畫匠,用最的筆墨勾出這幅圖來。四朵紅蓮,一朵含苞,三朵值了花期開的正盛。斜斜的出來,骨朵顯得,全開的花兒顯得堅韌,英氣。無無緣,倒也清心寡慾。
套上短,裹著巾子抱他出來,散發著溫熱的子著我,攥著我服前襟的一粒銅扣不撒手。從臉到子全是瓷白,白晃晃的小格外修長。
「為何要我紋?」他抬眼問我。
你生是我張啟山的死人,死是我張啟山的活鬼。生死我都要了,不留些記號怎麼行?
「好看。」我這麼說道。見他皺眉,估計是怕疼,又復安道:「不會太疼,忍忍就好,我在自己上試過。痛極了就停,改日再作,再說這圖也不是幾天就能完的。」
他執意要看我上所紋何,我只得了上,用手蘸了酒拍打大胳膊,不一會兒胳膊外側便顯出鋼印似的一個圓圈,裡面正楷一個「紅」字。
他手指尖一點一點的靠近,直到冰涼的上氣火旺盛的溫。怔怔地描摹了一遍紋痕,抬頭木木的問道:
「二月……『紅』?」
我點點頭,攬他懷,只是不知應當說些什麼。便任他那長眼睫刷子似的刮蹭膛,的。
二月紅呵……我何時能告訴你,張啟山早了了恨,那人命也早已不在乎,二月紅,回來罷。
他不是那疤痕質,趴在石板臺上,背部除了蝴蝶骨突出再無瑕疵,綿。頭髮順在一邊,側過頭看我。我起他的下頜,橫了只監獄常用的木在他邊,他含了去,免得咬到舌頭。
計劃紋從腰際開始,一花一籐的斜紋至另一側的蝴蝶骨,繞過肩膀一直到靠近左口的地方,用整朵紅蓮作為收筆。
自己不知在多人上練習過割線,只為了能掌握到最好的角度,恰到好的深度,和下針帶來的痛楚,如何能降到最小。
不願假於他人之手,說不清,只覺這是我要留得標誌,親手勾線上再到完,才算順理章。
我拍拍他的,明顯覺下的人全繃,示意他要開始了。畫好線的廓,拓印的非常相似,深吸一口氣,穩住手,下針。
「切忌勿太細,過淺,渾開。」醫生在一旁不斷指點,小心的運針,半刻不到便出了一汗。二月紅更是,冷汗一層一層,痛極皮上都起了一層小顆粒。
真是費神,可卻覺著不出有多累,明明比理軍務還要耗人。聽他咬著棒,一聲一聲的或輕輕□,或鼻腔悶哼,無一不使人張振的
小心下線,吸藥棉換了一塊又一塊,手心滿滿的全是汗。針尖挑破皮,提起來,總會晃一下眼睛,幾番下來眼裡明顯充,住眉心緩了好一陣才算過勁。
從腰際到後背中央的一部分勾線完,我如釋重負的呼出一口氣,且不說他痛的快要虛,僅我這施針的人都累的不願彈。打起神把他抱進懷裡,小心不到背,問他:
「疼麼?」
他點頭,都在,木棒將角磨得發紅。低頭慢慢咬上他的下,出舌仔細的著細緻的角。他環上我的脖子,冷汗出盡胳膊也是冰冰涼涼,抬起頭配合著我。神似乎有些異常,子一直痙攣著,我不停順著他的頭髮安,舌頭將他的牙齒一個一個的過,將他那的舌頭吸進裡,然後再頂回去,攪拌著。
安似乎起了作用,舒服的□從鼻腔和管傳出來,嗯嗯啊啊分外好聽,若不是念他後背的疼痛,真想在這兒要了他。。
叮囑他趴著睡,切勿沾了水,待醫生收拾好,我也將他安置好,他的頭髮,心想今天辛苦了。。
「走了,明日再來。」
他急忙雙手握著我的手指吃力的坐起來,疼得不住倒吸涼氣,握住不鬆開,問道:
「明日就來?」
看來真是刺疼了,他怕是自覺明日再來經不住,我只是想盡快紋好,明日晚,足夠了。
「明日晚上。快躺回去,莫要了風。」
他鬆開手,抬頭一直看著我,鬆了口氣似的,慢慢趴回床上。
為何要鬆口氣?出門點了煙解乏,不住的想著。。
我走了就這麼值得你放輕鬆?
罷,深吸一口煙,坐上車。
確實難得睡了個好覺,一夜無夢。
第二日下午便接了醫生驅車前去監獄,今晚有局應酬推不開,不願耽誤進程,紋這種事要速戰速決才好,拖久了反而容易風染
下通煙道的屋子還算暖和,只是到了夜裡不再燒炭火會覺得更涼些。進門時他還在睡,側躺在床上背對著我,被子搭蓋在上,出整個白的後背。可能是肩膀涼,他一手捂著自己的肩膀。繞到前面去,看樣子睡得並不踏實,皺了眉,長眼睫側面看起來一一,我他的頭髮,很快便醒過來。
含糊的不知說了句什麼,坐起來,長長的剛好夠不到地。趁他迷糊,我手托住他彎,避開後腰上的刺青將他抱了起來。換作清醒時不知有多不願意我手腳,這般溫順的模樣還真是有。
他尋死那段日子,我曾問過醫生怎麼才能把人變得麻木癡呆,聽話溫順,當時一是覺得罪人不該死,二是認為若是他能活生生的留在我邊,即使是個癡兒我也認了。
終究沒那樣做而選擇打了嗎啡,末了卻發現自己的還是從前那無慾無求的二月紅。慶幸沒選了什麼極端的方式,想到這裡收了胳膊,死死將他箍在懷裡。唉……二月紅。
「怎麼這麼早便來了?」他倚在屏風上,聲音還帶著沒睡醒的慵懶,的有一點啞。胳膊勾住他的小腹,用紗布蘸了酒幫他後背消毒,看不到臉也不知他是個什麼神,反問道:
猜你喜歡
-
完結19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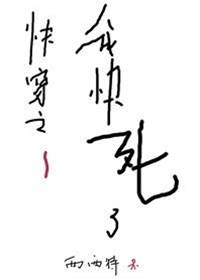
快穿之我快死了
我報考電影學院那會兒,主考官給我安排了場哭戲, 我把大腿擰青了都沒哭出來,現在麼,呵。 陳又叼著根煙,給我十秒,我能哭成狗,死狗。 444:影帝,該去下一個片場了。 0:本文攻受之間不存在任何血緣關係!!! 1:主受 2:作者邏輯死 3:無腦文,無腦文,這是無腦文! 4:精分攻,1v1 5:作者腦子有深坑,拒絕填補 6:全文架空 7:雙C控慎入
94.2萬字8.18 3476 -
完結399 章
地球贖回中
公元2222年,地球被群星屏蔽。 失去太阳,停止运转,全球灭绝性危机。 地球人唯一的机会就是潘多拉之盒。 参与盒中游戏,找到盒中丢失之物,赎回地球。 于是,地球人疯狂了。———————————————— 戏精附体爱财如命的宁不问打开属于自己的潘多拉之盒。 得到了属于自己的新手大礼包——一条柴犬。 开局一条狗,过关全靠吼。 面对这样惨淡的现实,宁不问在此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等我赎回地球,我就让所有地球人都给我交赎金!” “下一个全球首富就是我!”
103.8萬字8 2898 -
完結177 章
天仙老攻快死了!
秦淼是個顏狗,見到好看的人理智就自動下線。他快穿小世界救人,次次都被漂亮渣男迷住,不僅救人失敗自己也跟著便當。直到有一天他發現,自己要救的人才是真正的天仙。 秦淼:我要給他當老婆! ! ! 於是秦淼重新回去,發現天仙老攻快死了,立刻開啟狂暴模式! 【拯救豪門病弱少爺】短命家族搶我天仙老攻壽命?我來了,你搶了多少都得雙倍還回來! 【拯救血族污染的校草】放逐華國的血族咬我天仙老攻?我來了,梵蒂岡給你夷為平地! 【拯救眼盲廢太子】把我天仙老攻當妖星降世?我來了,這皇位你不想坐了就直說! …… 給天仙老攻遞花順手給漂亮渣男們發個便當。
43.7萬字8 2180 -
完結99 章

和校草聯姻之后
大一暑假,簡然和聯姻對象領了個證。 拿到紅本本,他拍了拍“老公”的肩膀:對了哥們,你叫什麼名字? “老公”眼皮微抬:自己看。 開學的第一天,室友告訴簡然他校草的位置被一個學弟搶了。 簡然表示懷疑:不可能!還會有人比你簡爸爸帥?! 室友把簡然拉去操場,指著全場最帥的那個男生:就是他! 簡然左看看,又瞧瞧,覺得有些不對。 ??? 這不是他那個只見過一面的老公麼! 簡然:叫學長。 任青臨:叫老公。 食用指南: 1.同性可婚背景/日常向小甜餅/日更HE
27.4萬字8 7393 -
完結39 章

恃寵而驕
明星受小人得勢氣焰囂張, 別人以為是仗著金主的寵愛恃寵而驕,其實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娛樂圈背景,明星受 金主攻,包養出真愛,狗血有
9.4萬字8 40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