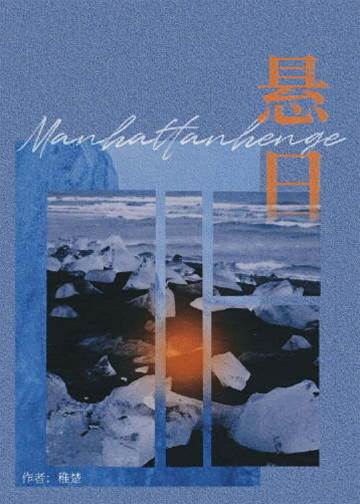《裴公罪》第11章 其罪十 · 不義
裴鈞聲音一落,他后余下的六部諸人即刻接連附議:
“臣表票。”“表票。”“臣亦表票。”……
這一聲接一聲的表票順應天心、閣議,直如一條寬廣大河匯滾滾東流之水,無疑將新政的推行化為定局——而當所有人都向前出這一步時,朝堂上那唯一一個止步不前、沒有附議此策的晉王爺,自然就了這奔騰洪流中無比醒目的阻浪礁。
裴鈞再抬了眉向金柱后去,果見皇親列座之中,晉王也正向他看來。
晉王在笑,哪怕已是被裴鈞的無信之舉害了日后的眾矢之的,他笑得也極漠然,眼下倏地與裴鈞目相遇,他甚至全然沒有任何不豫般,只遙遙端起手中茶盞,風度萬千地向裴鈞一敬,又繼續與側泰王言談。
大殿上已經再度沸議起來,幾乎所有人都來回看著閣尾座的張嶺和六部當頭的裴鈞,皆道這師徒二人為了新政之說吵嚷至今,是連師徒恩義都吵斷了幾乎反目仇,怎生這裴鈞如今卻變了褂,又要幫起新政來了?
閣九座中的張嶺也是滿目錯愕,此時一張冷臉向對面遙遙站立的裴鈞,已了笏板前傾子。
九座之首的蔡延灰眉一抬,不聲將此二人行狀收眼中,又垂了眸不發一言,他邊,東殿大學士蔡飏聚了眉頭靠近過來,在沸人聲中低了嗓子:“父親,如此我們行事或然就有變了。”
蔡延沉一聲,依舊似閉目養神般悠悠坐著,口中只輕言一句:“裴家這小子醒了,想明白了,這是要來搗了。”
本朝立國以來講究理學,崇尚“與君同治”,不僅存續了閣之制,甚弘揚了票議之道。取于民,亦用于民,朝廷此舉可示天心與民意同在,是順民而為,故前幾代帝王雄才偉略、福壽延年,功偉績自由此建下,可到了姜湛的父皇肅寧皇帝一朝,君王多病弱難以掌權,朝中政事便漸漸由閣包攬。直至肅寧皇帝駕崩前后,原定登基的皇太子姜滸忽被其宮人告發了巫蠱詛咒先父一事,被褫奪了繼承皇位的資格,朝中便一時大。經過一番驚魂暗變,閣重臣與皇親協議,挑選了皇后次子姜湛繼位,又本著帝年、需要輔佐的道理,自然又謹慎經營,將朝政握于手中。
Advertisement
姜湛登基八載以來,閣之中雖小有更迭,常駐的九位閣部卻仍舊還是三公與六大學士。此九者多由德高重、門生廣布的員充當,其中主力諸以蔡延為首結一派,早已依靠票擬權和盤桓朝中的錯綜關系架空了皇權。而閣的決策,又總還需要五寺、六部來執行,故前世的裴鈞進六部后,為使姜湛得力與閣抗衡,便各苦苦鉆營,利用曾在青云監中與他同屆、異屆的種種人脈打通了六部,將六部眾人結為一 黨,一旦政見有異,便可借由票議之制與閣隔朝對立,以保存己方的利益,雖其中每一人的階都不如閣九位閣部,可當他們聯結起來,卻可以左右朝中大半實權的流。
如此,朝廷便有了這樣幾個派系:一是帝姜湛皇權之下的皇親和以張嶺為首的學派清流;二是以蔡氏為首的重臣、州;三是以裴鈞和六部為首的一 黨中游員,后也稱裴黨;四便是與晉王姜越關系較近的皇親與兵力——他們中大部分沒有票議權,雖無法與朝中文的政策決議相較量,卻可讓朝政的每一步都走在鐵掌翻覆的后果前。
每當朝廷出現新政、新策或變法之說,天子都會給百票議,那麼有票議權的員自然都會忐忑思索如何在朝中各個派系里站隊、保,而他們的忐忑,自然來源于他們所關注的新政的敗——
他們關注新政功時他們所在的權勢陣營是否能獲益、能獲益多,也關注失敗時他們能否保命或會否失去什麼。一部分的員實則只是從眾地做一個決議,去保證自己能在朝中立足,而本無力顧及這決議會要多百姓與疆吏州熬紅眼、丟了命,而另一部分被從眾者追隨的重臣中,絕大多數也只在意一個結果,只有極數的人會關注過程。
Advertisement
前世的裴鈞年紀尚輕,眼界尚淺,沒能為這極數人之一,可蔡延卻是這極數人中的佼佼者。他正是因為預見了薛、張二人提出的新政中可以攫取巨大利益,便至始至終大力支持,如此就取得了新政的主導權,在短短幾年,更使蔡氏枝葉散布各、愈發壯大,若不是裴鈞后知后覺極力發展實權派員與之角力,那十年之后江山社稷改名換姓或非奇事。
這一世的裴鈞深諳此理,自然就要先發制人。
此時,六部的表票讓五寺諸間約傳來一陣長息,皆為了一時茍安的立之到慶幸,而座之上,帝姜湛扣龍椅的指尖慢慢恢復了,終至放開,收回袖中,連帶繃的肩線也松弛下來,角漸漸揚起笑意。
朝會在頭接耳中散了。吏部尚書閆玉亮領著工部二人開了馮己如,共裴鈞一前一后往外走:“子羽,今晚我與大理寺李斷丞約了酒,來麼?”
裴鈞好笑地看他一眼:“到底是師兄的手腳快,這就活絡上了。”
“既都上了一條船,自然要比閣那幾位捷足先登。”戶部侍郎方明玨也跟上來,嬉笑著一點閆玉亮的肩,“都是同屆的,你怎麼就他,好歹也帶上我唄?我再捎幾個鴻臚寺的小兄弟,咱行酒令!”幾言幾語這酒桌子就越約越大,說著他還拉上了本部尚書大人,又問后:“師父也去吧!”
刑部尚書崔宇年紀稍長些,寡言莊重,聽言與本部侍郎對過一眼,輕輕頷首,往后看向兵部二人:“師父和蔣老也一道兒罷?”
他師父兵部沈尚書年過五十,直說子不大當得住,擺擺手:“總歸過幾日咱們還要聚,今兒就算了吧,你們小輩玩兒去。”
Advertisement
旁蔣侍郎比他年輕不了幾歲,便也說罷了,趁著眾人一齊出殿的當口,只踱到裴鈞邊兒問:“裴大人,那犬子來年恩科之事……”
“蔣老有這話,早說就是,送東西豈不生分?”裴鈞抬手拍拍他右臂笑,“晚輩可萬萬當不起。”
場面話說出來,蔣侍郎亦心知肚明,只道“一點兒心意罷了”,又說事后還有重謝,只勞裴鈞費費心思,激不盡。
裴鈞與六部諸三言兩語這麼搭著,走在清和殿外的石階上一抬頭,正見前面一道石青的影子就要下階走長廊了,連忙出聲道:“晉王爺留步。”
可前方的晉王都未頓,就似未聽聞般,徑直又要隨眾皇親下行。
裴鈞無奈一笑,只好別過六部人等,腳下趕兩步,提聲再喚:“晉王爺!晉王爺留步!”
這一聲是周遭親貴全都聽見了,不免都側目看向晉王。晉王這才不得不告別眾皇親,止步負手回過來,將寒氣在淡笑下,靜靜看向快步行來的裴鈞,佯作惋然地長嘆一聲:“裴大人可把孤害苦了。”
裴鈞握了笏板袖住雙手,笑盈盈對他一揖:“臣何德何能,王爺可冤枉臣了。”
晉王吃了裴鈞那“不能反票”的暗虧,自然在被裴鈞出賣的一刻就醒悟過來,此時笑得就更淡漠些,斜睨他一眼,涼涼開口道:“朝中皆道裴大人是結黨營私,是佞,孤原想裴大人雖生各、弄政如,可于這新政之策卻總還存有一爭之勇,大抵只是個的罷了,今日卻未料……裴大人還是個瞎的。”
裴鈞聽言一頓,不由咽下了本要說出的言語,直看向晉王,頗委屈道:“王爺,臣班為臣這些年,所見者一眼家國朝政、一眼明君萬歲,于禮部兢兢業業、于京兆廢寢忘食,縱有耳不聰、目不明,又如何能瞎了呢?王爺這是又冤枉臣了。”
晉王不置可否輕笑一聲,抬眼再看向他時,那眸中冷厲之一閃而過,余下的也不知是哀其不幸還是怒其不爭,最終只出口的寒意里:“裴大人好一口伶牙俐齒。既裴大人還不知是瞎了哪只眼,那孤今日就送裴大人一份兒好禮,幫裴大人揭了頭上那蒙眼布,好好清醒清醒。”
說完,他也不待裴鈞再講什麼,轉就走下石階了長廊,徒留裴鈞立在早朝散盡后空空的大殿前,著那再度沒皇親之中的俊背影,漸漸挑起長眉,滿心莫名其妙。
再到禮部打過一頭,出了皇城又是午后。裴鈞心里揣著要替晉王爺逮鴨子的事兒,亦想著要為日后吃下吳廣鹽業鋪鋪路子,便又上了轎,說去趟老友曹鸞的府邸。
冬日微暖的日頭碎碎灑在轎面兒上,搖搖晃晃就到了城南一座烏門宅院前。院門上牌匾樸拙無框,甚可見有道裂木橫紋,卻依舊拿大筆寫了“曹府”二字,似是無意,卻顯幾分落拓。
里頭很快迎出玲瓏家丁,引裴鈞一門廊即可覺出腳底生暖,想是地龍已然早早燒上,更聯通了火墻暖爐,他進了前廳喝過茶更覺出分兒熱,解了狐裘坐聽邊的西洋鐘滴答作響,剛將滿室琳瑯玩意兒瞧上一遍,便等來個高大俊逸的男人踏廳里笑:“裴大忙人,稀客啊,你這一來,我是連個午覺都不能睡了!”
裴鈞笑眼睨著曹鸞進來,坐在椅上也沒起:“哥哥這麼個金缽缽,一覺得睡沒了多銀子?倒還是別睡了罷。”說著寒暄道:“嫂子和萱萱呢?”
“后院兒收東西。”曹鸞濃眉一舒坐在與他隔桌的椅子上,端過家丁正好奉來的熱茶,喝了一口醒神,“正好年底,們回娘家瞧老人,恰我后日要下江陵辦事兒,就帶們一路。”
說著,他斜眼一瞥裴鈞,怪道:“這都要走了,你又給我添什麼事兒來?不會是今兒新政表票的事兒罷?聽說也沒有個反票的要擺平,你能惹了誰?”
裴鈞聽言,竟手就要去撓他耳朵,“哥哥你這耳朵也太長了,還是剪一截兒罷,省得晚上睡覺打著嫂子的臉。”
“去!別鬧。”曹鸞擱了茶一把打下他手,好笑起來,“這大的事兒我若不管,那我生意都別做了等著關門兒罷。你到底找我什麼事兒?再不說我要收你錢了。”
“別別別,我說我說。”裴鈞收回手來支著桌,說回正事,“我來請哥哥幫我逮些好看的小鴨子,要白兒的。”
“……小鴨子,好看的?”曹鸞定定看他一會兒,微瞇起眼睛,過了會兒才深意點頭,再次端起茶來喝:“行,要多?”
裴鈞想了想:“總得要個幾百——”
“咳!咳咳……什麼?”曹鸞登時就被茶給嗆住,好不容易順了氣,抬眉上下打量一圈裴鈞的板兒:“你這都多久不沾腥兒了,幾百……能得住麼你?”
“嗐,我要的是真真的白兒鴨子,不是你那些賣皮兒的小人。”裴鈞是真服了曹鸞這污七糟八的腦子,直嘆果真和梅林玉估得一模一樣,于是就把話說清了:“前幾日我在青云監把晉王爺的鳧靨裘打臟了,托了梅爺替我修,他就找不著那麼多鴨子,這才讓我來麻煩你。”
曹鸞恍然大悟,嘖嘖稱奇:“原來是那件兒裳——那你可真是撞‘大運’了。備好銀子吧,那裳貴的不是鴨,是藥水兒。”
裴鈞毫不疑曹鸞的言語,原也做好了為救鄧準折費千金的準備,此時便只道:“你給個數,不我就只能抱著晉王爺的彎子哭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18 章

勢不可擋
“哥,我又看上一個男人,你幫我牽牽線吧。”冷臉沉默。“他是皇城根兒下的太子爺,根正苗紅的權三代。”冷臉沉默。“他長得帥,人品好,無情史,無惡習,而且至今還是個處!!我保證你看到他第一眼就會喜歡上他的。”一年後,哥哥把這個男人追到手了。
48.1萬字8.09 4513 -
完結239 章

惡毒男配不爭了
生前,晏暠一直不明白,明明是一母同胞的親兄弟,為何父母總是偏愛弟弟,把所有好的都給他,無論自己做什麼都得不到關注。 越是如此,晏暠便越是難受,越是不平,於是處處都和弟弟爭。只要是弟弟想要做的事情,他也去做,並且做的更好。 但明明他才是做的更好的那個人,卻始終得不到周圍人的認可,父母,老師,同學,朋友望著他的眼神都是嫌棄的,說他善妒,自私,喜歡搶別人東西。 一直到死,晏暠才明白,他搶的是主角受的東西。他是一本書中為了襯托主角受善良的惡毒男配,是為了讓主角攻出現打臉,在主角受面前刷好感度的砲灰。 重生回來,晏暠一腳踹開主角,誰特麼要和你爭,老子轉個身,你哭著也追不上我。 他不再爭,不再嫉妒,只想安靜的做自己。讓自己的光芒,照在關注他的人身上。 = 很多年後,有人問已經成為機甲製造大師的晏暠。 「您是怎麼走上機甲製造這條路的?」 「因為遇見了一個人。」晏暠。
56.1萬字8 37239 -
完結107 章

辣雞總裁還我清白![娛樂圈]
十七線演員梁宵出道五年,不溫不火。 因為被拍到頻繁出沒星冠影業總裁別墅,全網一夜成名。 別墅臥室裡,梁宵洗乾淨趴在枕頭上,專心致志抱著手機打遊戲。 “總裁,您咬好了嗎?咬好我就下班了。” 2. 作為星冠影業總裁,霍闌有個秘密。 他是個特殊變異型alpha,只有定期標記吻合的omega,才能維持信息素穩定不失控,否則就會危及生命。 霍總裁不近O色,第一天見面,就把銀行卡跟合同冷漠地推到了梁宵面前:“各取所需,不該想的別肖想。” 梁宵勤勤懇懇挨咬,踏踏實實拿錢,安安心心打遊戲。 直到他在星冠影業投資的大製作裡一炮而紅。 面對鋪天蓋地的包養黑料,梁宵跑回家翻出合同,準備讓總裁幫他澄清真相。 霍闌眸色沉沉,接過合同,當著無數鏡頭話筒揉成一團,把人拉回身邊。 “別慌。”梁宵被掐著腰按在牆上,冷靜抱住把臉埋在他脖子裡的霍總,沉穩地轉向經紀人,“他現在要還我清白了。” 3. 經紀人瘋了。 【悶騷冷清總裁攻x碎嘴沙雕健氣受】 【abo無生子,輕鬆放飛小甜甜甜餅】
43.9萬字8 3232 -
連載647 章
獸王
在普通人世界中存在著一個很少人知道的異類世界,他們的身體中有著常人無法企及的力量,這種力量被他們稱之為暗能量 因為暗能量的不同,他們將學會不同的駕馭方法 這些古老的力量可以幫助他們駕馭各種偉大的生物,甚至能模仿這些生物的能力,變成它們的樣子,不過這隻有極少數的傑出人物才能辦的到。 ……
151萬字8 122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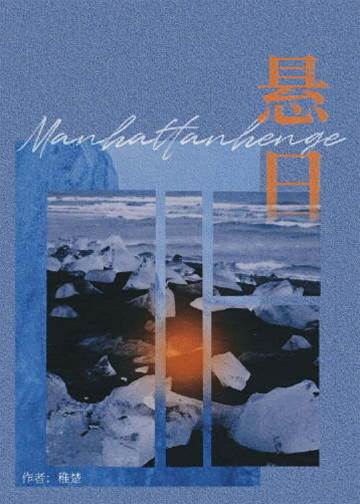
懸日/戒斷
別名:戒斷 寧一宵以為這輩子不會再見到蘇洄。直到酒店弄錯房卡,開門進去,撞見戴著眼罩的他獨自躺在床上,喊著另一個人的名字,“這麼快就回來了……”沖動扯下了蘇洄的眼罩,可一對視就后悔。一別六年,重逢應該再體面一點。…
49.4萬字8 4350 -
完結228 章

前夫高能
混血小狼狗李維斯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因為簽證到期,只好找人假結婚以取得中國綠卡。本以為只是一場單純的交易,誰知卻卷入離奇的超自然案件,各路奇葩排紛紛找上門來,拜倒在他的破牛仔褲下。當然,他們拜的不是他,而是他身后的準·老公。本文主要講述失業菜鳥和作妖大神先婚后戀,夫唱夫隨屢破奇案的溫馨(?)婚戀(?)懸疑(?)故事,年上,深柜,甜寵,暖男奶爸小狼狗×作妖任性大灰狼,也叫《不差錢夫夫花樣探((常》。近未來架空,涉及國家地名學校組織等均與現實無關,切切!—————————*謝*絕*扒*榜*———————...
82.7萬字8 34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