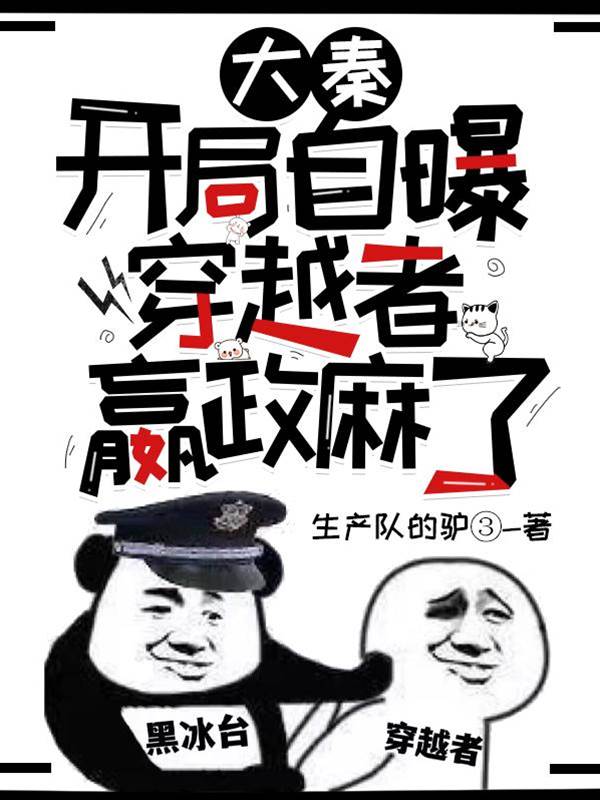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貼身丫鬟》 第105章
時硯開了門, 夏了,他穿的服不厚,臉上蒙著面巾。面巾是傅慎時讓他戴的,他若病了, 就沒有人能伺候傅六了。
時硯的眼神里, 添了一抹死寂,比從前更執拗幾分。
他開門不是為了放殷紅豆進去的, 他雙手還攔在門上,扭頭隔著屏風,沖里面道:“六爺,是。”
傅慎時也不驚訝,除了殷紅豆, 還有誰這個時候敢來?
但他心中還是歡喜的。
傅慎時躺在床上, 和門之間隔著一道屏風, 兩邊相互瞧不見。
他的聲音喑啞而冷淡:“把門關上。”
這是要趕走。
殷紅豆站在門外,他的嗓音緩緩地傳的耳朵,仿佛年行將就木的老者,的心猛然一揪。
時硯作勢要關門,殷紅豆下意識手抵擋住了, 時硯便狠狠地推了一把,殷紅豆沒站穩, 往后退了幾步, 靠在長廊的木柱子上, “砰”得一聲, 門就關了。
冷風陣陣,殷紅豆的脖頸很涼,廊外的天空漆黑如墨,一彎月懸空,沒有一顆星子,伶仃卻更顯明朗。
上房的燈還是亮著的,殷紅豆走到窗戶邊,敲了敲窗,朝里邊兒道:“傅六,我有話對你說。”
里邊很久沒有靜,就靠在墻上,耳去聽。
房里傳出料的窸窣聲音,殷紅豆知道是傅慎時起來了,等了一會兒,高麗紙糊的窗戶暗了一些,像是被人擋住了,過了一會子,又更亮了,因為傅慎時時硯多拿了一個燭臺過來。
傅慎時披頭散發地坐在羅漢床上,側頭定定地看著窗外的倩影,這是他朝思暮想的姑娘,如今只與他有一墻之隔,他卻不能見。
他低了頭,低低的聲音傳出去:“你說吧。”
Advertisement
殷紅豆靠著墻,抱著手臂,單腳點地,隔著窗戶,道:“發痘了嗎?”
“還沒有。”
“哦。”殷紅豆頓了一會兒,又道:“莊子上我都料理好了。”
“嗯。我猜到了。”
殷紅豆像是與他面對面說話一樣,還抬了抬頭,問道:“那你猜到我怎麼代的嗎?”
傅慎時看著窗戶紙搖頭,道:“只能猜到七八分。”
殷紅豆便將自己代給汪先生的話,說給了傅慎時聽,他還和以前一樣,沒有意見的時候,只是聽著,待說完了一句,才去接的話。
莊子上的事,殷紅豆已經理的很好了,傅慎時無可挑剔,隨后他又問:“你是來問我以后怎麼置莊子吧。”
殷紅豆聽了傅慎時用代后事的口吻說話,心口有些發疼。
傅慎時卻沒顧忌,他似乎很坦然,聲音也輕緩:“都給你理,莊子和發財坊,你想怎麼理就怎麼理,有汪先生他們,也不必多擔心。京城里的鋪子,替我給我三哥,只當是報答……傅家對我的養育之恩。”
明明是很尋常的語氣,殷紅豆卻不自覺地哭了,沒哭出聲,只是眼淚一顆顆地往下掉。
傅慎時繼續道:“你也已經看過我了,足夠了。明天醫會過來,你一道出去。”
殷紅豆搖了搖頭,道:“明天我不走。”
傅慎時哽咽了,他凝視著窗戶上的人影,側著頭,一顆圓腦袋,不是雙丫髻,就隨便捆在腦后而已,長卷的睫一下一下地眨著,鼻尖略圓,微嘟,尖尖的下。
他忍不住抬手去輕,著聲音道:“你別犯傻。”
殷紅豆終于控制好了緒,低著頭,用很平和的語氣道:“我不是為了你,我是要從你上取痘漿,給我自己接痘,接了痘,我就再也不會得天花了。若這個法子了,莊子上的人也可以用。疫病已經發了,難得逃過去,只有接痘才能活命。”
Advertisement
傅慎時一笑,道:“你別哄我了……從前你的花言巧語我不是不知道,不過是放縱你,這次我不會信你。”
殷紅豆抿了抿,細聲道:“沒有哄你,說的是真的,得過天花的人,若是活了下來,不會再得,這你總該知道吧?接痘同理,接了痘,死不了,卻不會再得。”
傅慎時臉上笑淡了,道:“死不了?”
殷紅豆糾正了一下:“也不是完全死不了,但極有可能不會死。得天花也分個輕重,輕的就不會死。”
傅慎時聲音像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縹緲凄涼:“得天花不死的人,幾乎未曾聞得。即便不死……你可知道活下來是什麼樣的……怪。”
天花不單是長在上,是會長滿全,包括臉上,得了天花,渾發,巨無比,即便能活下來,也會留一的疤痕。能活下來的人,也沒有個人樣,丑陋如鬼。
傅慎時失了雙而已,這七年來,就遭了那麼多不公,這回即便是逃過了疾病的厄運,隨后要經歷的東西,恐怕會他生不如死。
他大抵,更愿病死。
天道不公。
殷紅豆眼淚流得更兇了,抬手抹了抹眼淚,道:“明天醫會來,醫會告訴你,我沒有騙你。”
傅慎時到底沒有信,只道:“明天老老實實地走,我如今這樣,你若執意要留下來,你將來若無事……你可知道會是什麼下場?”
殷紅豆道:“哎,不跟你說這個了。我就是要走,我這個份也走不,最后還不是會被揪回來。”
傅慎時的手在窗戶上,他道:“我代過我三哥了,讓他放你歸良。手足一場,他應下了就不會反悔,這次你大可放心的走。”
Advertisement
說完,傅慎時打開桌上的木盒子,隔著干凈沒用過的帕子,拿起里面折一指寬的賣契,通過窗戶塞了出去,他道:“既你來了,這個你自己拿著。”
殷紅豆抬眼,半截紙從窗戶里出來,手去拉,只拉出來大半截,就拉不了,還有一小截,被傅慎時地住。
這是他與,最初的羈絆,也是最后的。
放了自由,傅慎時與殷紅豆,就再無牽扯,自此以后,想走就走,想嫁就嫁。
殷紅豆著大半截賣契,用了點力,也沒有太用力,這樣拉扯著,就能到他的力道。
賣契如一條紅繩系著兩人,此刻卻要斷了。
傅慎時指頭輕,他要死了,才發現……竟然最是舍不下,他的夙愿,不過是放離開,祈求能平平安安而已。
他語氣略有些調侃,道:“紅豆,你若早些以死相,我指不定已經放了你……”他又用低啞的聲音,道:“那天是我做的不對,我惱了才會說氣話,我從前對你說的話都是真的,我沒想過違反諾言。你不要恨我了,好不好。”
殷紅豆淚眼朦朧,沒心思在這個時候還特意去計較這個,咬著,不出一點聲音,肩膀卻在輕輕地抖。
傅慎時又上娟秀的影子,溫聲道:“我都替你了了心愿了,怎麼還哭了呢。”
殷紅豆皺了半截賣契,過了很久才平復下來,抬起頭,就看到窗戶里邊,傅慎時的手掌在上面,也出手,隔著窗戶,他的掌。
傅慎時看得見的手,他著窗戶的手,更用力了,與此同時,他松了另一只手。賣契像一條魚一樣溜出窗戶,到了殷紅豆的手里。
Advertisement
他道:“賣契我時硯取出來,隔著帕子拿的,我手上還沒有長疹子,你了應該也不會有事。”
賣契在殷紅豆的手里變了皺的一團,道:“……好。”吸了吸鼻子,問他:“疹子都長哪里了?”
“上和上,手臂上,手腕上好像也冒出來幾顆,臉上還沒長。”傅慎時語氣微頓,有點兒孩子氣地道:“希臉上不要長,一顆也不要。”
他從前倒不多重相貌,如今卻想著,便是死了,面容也不能太丑。
殷紅豆很快接了話,道:“臉上不會長的。”
兩人沉默了許久,雙掌仍舊隔著窗戶相,一指頭對應地著對方的指,若是沒了窗戶阻隔,十指必會相扣上。
殷紅豆先開口道:“我問了翠微們,你不在的時候,院子里有人進來過。”
傅慎時道:“我知道,只我一人得了這病,定然是府里有人做鬼。”
殷紅豆皺了眉頭,道:“天花都還沒傳京,如真是傅二所為,他倒是真有能耐……也真夠心狠手辣。”
傅慎時冷笑道:“疫病在南方早就傳開了,想取痘漿也容易。他恨不得我死,想置我于死地,想方設法做到也不足為奇。”
殷紅豆默然,傅二恨極了傅六,說到底,還是為了,問他:“你會放過他嗎?”
傅慎時知道的子,他想報復傅二,卻不想殷紅豆替他出手,便答非所問:“外面冷嗎?”
“還好,都夏了,能有多冷。”
傅慎時道:“你今天肯定來得不容易,趕去歇著。”
殷紅豆道:“坐馬車來的,除了有些顛簸,倒也不覺得累。”
傅慎時在里邊兒道:“我累了。”
他收回了手,被時硯扶著下了羅漢床。
殷紅豆再站下去只能吹冷風而已,便也回了原先住的廂房。
猜你喜歡
-
連載1439 章

妃常想休夫
天才神醫冷清歡一穿越,就給大名鼎鼎的戰神麒王爺戴了綠帽子,肚子裡還揣了一顆來曆不明的球,從此每天都在瀕臨死亡的邊緣小心試探。麒王爺自從娶了這個不安分的女人進府,肝火直衝腦門,時刻都有掐死她挫骨揚灰的衝動。後來肝火變心火,心火變腎火,腎火變成揭竿而起,將她盛進碗裡的勇氣。冇見過這種世麵的冷清歡被嚇得爬牆逃了,揚言休夫改嫁。麒王爺悔得腸子轉筋,因為他橫豎看不順眼的那顆球,竟然是自家老爺子早就盼得眼紅的金孫。衝冠一怒,十萬鐵騎,踏平臨疆,搶婚成功的麒王爺笑得像個傻子。
147.4萬字8 172426 -
完結4128 章

武神空間
葉希文本隻是地球上一個普通的大學生,卻意外穿越到了一個名為真武界的世界! 在這個世界中,強大的武者能翻山倒海,毀天滅地! 本是資質平凡的他,因為得到了一個神秘的特殊空間!任何的武學都可以在神秘空間中推演,別人修行幾十年,他隻需要一年! 隻要有足夠的靈石,什麼天才在他的麵前都是浮雲!
1094.5萬字8 193923 -
連載252 章

大唐仙醫
太坑爹了,居然穿越到一個馬上就要砍頭的犯人身上!面對即將砍落的屠刀,張小霖如何自救?
41.7萬字8.18 15811 -
連載118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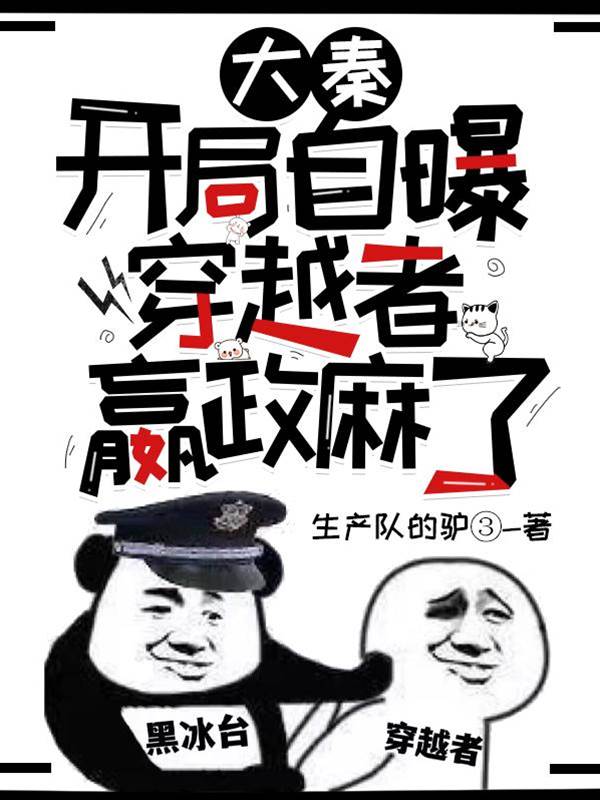
大秦:開局自曝穿越者,嬴政麻了
始皇帝三十二年。 千古一帝秦始皇第四次出巡,途经代郡左近。 闻听有豪强广聚钱粮,私铸刀兵,意图不轨,下令黑冰台派人彻查。 陈庆无奈之下,自曝穿越者身份,被刀剑架在脖子上押赴咸阳宫。 祖龙:寡人横扫六国,威加海内,尓安敢作乱犯上? 陈庆:陛下,我没想造反呀! 祖龙:那你积攒钱粮刀兵是为何? 陈庆:小民起码没想要造您的反。 祖龙:???你是说……不可能!就算没有寡人,还有扶苏! 陈庆:要是扶苏殿下没当皇帝呢? 祖龙:无论谁当这一国之君,大秦内有贤臣,外有良将,江山自然稳如泰山! 陈庆:要是您的贤臣和内侍勾结皇子造反呢? 祖龙:……谁干的?!我不管,只要是寡人的子孙在位,天下始终是大秦的! 陈庆:陛下,您的好大儿三年就把天下丢了。 祖龙:你你你……! 嬴政整个人都麻了!
247.2萬字8 9830 -
完結600 章

大唐:我被長孫皇后看上了
穿越大唐,系統還未激活,蘇牧在教坊司混吃混喝。幾日時間,便達到白嫖王柳永的境界。更斗酒詩百篇,驚徹長安。“趙國公府管事,替我家小姐提親,我家小姐才貌雙全。”“在下任城王府上管事,也是提親而來,我家郡君名為李雪雁。”“隴西李氏,我家大小姐傾慕公子已久,愿與公子喜結連理。”正被接連提親時,身披甲胄的兵衛涌入,將蘇牧圍住。端莊靜雅,鳳目含威的長孫皇后款款而來。“這個少年本宮看上了,帶回去。”
102萬字8 3179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