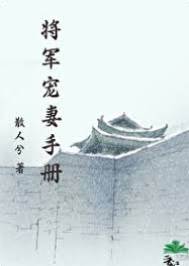《穿到大佬黑化前》 第78章
桌上放著水果,還有一大摞補習資料和這周落下的作業。
時暮看的腦殼疼,抓起一本翻了翻,扭頭道:“不用給我補了,我都會了。”
傅云深把藥片遞給,“作業要寫完,周一要過去,再過兩周要期末考試了,你認真點。”
……五天的作業。
時暮沉默了,抬眸:“云深哥哥,你幫我做吧。”
傅云深冷笑:“憑什麼?”
時暮:“憑我長得好看。”
他掐上了臉蛋,“憑你不要臉。”
電視機開著,傅云深轉到了新聞頻道,這是擺明不做作業不給換臺了,嘆了口氣,拿起筆不愿補著作業,高中題對時暮來說沒任何難度,三下兩下做了一頁。
懶洋洋打了哈欠,突然覺屁一,有人了過來。
時暮皺眉,目不由落在了傅云深上,他正低頭刷綠jj,時暮還瞥到了書名《穿到大佬黑化前》,名字很智障,文章很涵,神的文,最喜歡看。
那雙手又是一,甚至往花里去了。
時暮悶哼聲,又看向了旁貝靈,小姑娘看著新聞出神,時不時笑兩聲,傻乎乎的。
目向下,時暮注意到的手不住往上索著。
靜了幾秒,時暮低聲問道:“貝靈,你干嘛一直我屁?你就算了,你干嘛捅我花?”
話一出口,客廳里的三人都看了過來。
貝靈歪頭,眼神茫然:“我沒有你屁。”
時暮手一指。
這下不是屁了,而是大,正往腰上面的。
貝靈瞪大眼,驚呼聲,著急把手收了回來。
臉蛋微紅,心中忐忑,眼里布了層輕薄的水汽。
一直躲著時暮和傅云深的周植瞬間跳了出來,驚聲道:“我就說有人我屁,原來是你的!靈靈,你好啊!”
Advertisement
貝靈瘋狂搖頭,“我沒有我沒有,我沒……”
剛巧夏航一路過沙發,貝靈眼一掃,一只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掐上了夏航一屁。
“……”
氣氛就此陷尷尬。
瞳閃爍,用另一只手死死把這只手掰了下來,哭喪著臉:“我……我沒想你屁。”
表看起來快哭了。
夏航一蹙眉,彎腰輕問:“你是不是吃什麼東西了?”
貝靈搖頭,眼角閃爍著淚花,“我不知道,我控制不住我自己。”貝靈眼淚朦朧看著夏航一,“航一,你能再讓我一下嗎?就一下下。”
小眼神特別委屈。
“……”真可,夏航一差點沒把持住答應,還好他和傅云深不一樣,他是個正經人,想也不想就搖頭拒絕了。
時暮沉思半晌,試探說,“我窗臺上那個罐頭瓶子,你沒吧?”
貝靈按著手搭搭,“我就、就嘗了一小口。”
時暮和夏航一倒吸口涼氣,千防萬防竟然還沒防住?還嘗了小口?
夏航一抓起貝靈的小手,過眼,果然看到指頭上黏了很小很小一個黑點,這是鬼的殘魂,細微到讓人難以覺察,沒想到就是這麼一點殘魂就影響到了貝靈,同時也慨這鬼是真,死了也不忘借著別人發。。
他找來符紙,小心把那點殘魂弄了下去,嘆息聲蓬松的發,安道:“沒事了,你以后不要這些東西了,也不要吃,幸好時暮都吃了,若你真吃進了肚子,可不是人屁這麼簡單了。”
貝靈搭搭點點頭,又看向時暮,“時暮學長,你把擾我的鬼吃了嗎?”
時暮眼神游離,嗯了一聲。
貝靈咬,一本正經:“你要是喜歡吃鬼,以后我多勾引幾只,讓夏航一全抓來給你下飯。”
Advertisement
夏航一忍不住想笑,“你那天不是還說最怕這個了。”
貝靈語氣驕傲:“給時暮抓的,我就不怕。”
他抿,按捺不住微的掌心,輕輕了的小腦袋。
周日,時暮去醫院復查,吸收完一只鬼,腳差不多全好利落了,醫院醫生暗暗咂舌的恢復速度。
檢查確認完沒問題后,時暮和傅云深一同前往學校,剛回宿舍整理完東西,老黃就把時暮了過去,之前參加的廣播比賽獲得了一等獎,為了獎勵帶傷參賽的拼搏神,舉辦方還額外給了一萬元獎金,這倒是讓時暮欣喜不。
分給貝靈一部分后,時暮共到手五萬五,對來說已是一筆不小的財富了。
周植估計是長了一對順風耳,時暮的錢款剛到賬,沖宿舍的周植便咋咋呼呼的在耳邊嚷:“請客!”
這小子的嗓門又又大,震的時暮耳疼。
急忙往后撤了下,“請請請,你先離我遠點。”
得逞的周植笑的開心,語氣膩味不:“我找到一家帶ktv的中式餐廳,等下周考試完我們再去那兒慶祝。”
時暮連連點頭,周植的臉:“你是大侄子,都聽你的。”
給點就燦爛的周植笑的更耀眼了。
轉眼就到了期末考試,不管那個學校,考試和考試后的氛圍都是最焦灼難耐的,萬眾矚目之中,績公布。
只是這一次的全年級第一都讓人驚訝了。
時暮,傳說中緋聞不的轉學生。
的考試績讓整個學校都震驚了,三大主科有兩科目分數全滿,語文失誤了五分,各項加起來總分700,甩第二名整整三十分,沒錯,那個倒霉蛋第二名就是傅云深,第三第四都是一班的尖子生,跟著第五名是夏航一,夏航一各科目都考的不差,就是被英語拉了后。
Advertisement
這三人都是415的,還都是十五和十四班的刺兒頭,能考這樣不得不讓人咋舌。
當然也有一個意外,那個意外就是周植,考了全年級倒數第一,兩個第一都被415寢室占了,真是牛大發了。
作為一直被嘲諷績的英南十五班,當下就有人把績單到了高校論壇,同時還有時暮1080p的高清照片。
[誰說英南無學神,暮哥一出誰與爭鋒?]
十五班也不懂低調為何,先用一千字華麗辭藻稱贊了時暮的,又三百六十度分析了時暮績,最后得出結論,你們其他高校的都是渣渣,我們時暮一個打倆。
事實上時暮的確上相,經過一個學期的刻苦鍛煉和每周的鬼魂營養小套餐,的高從一開始的163竄到了如今的175,長手長腳,白紅,濃眉有型好看,上勾的桃花眼風四起,薄運衫下若若現的馬甲線無比。
[錦橙小仙:700分,p的吧?]
[我也覺得錦橙小仙:我是英南學生,真不是p的。]
[喵嗚:看臉后我覺得我可以,看到績后我覺得我不行。]
[嗷嗚:等等,這個臉有些眼!]
[一劍寒霜:臥槽,好像時黎,嚇了一跳還好不是。]
[看見我棺材了嗎:700分有點牛了啊,都快超過一中傅云瑞了。]
[dxhauobn:今年傅云瑞和時黎好像都是一個分數吧?]
[用戶7454:只有我注意到這個名字和那個混混一樣啊。]
[用戶2333:得了吧,可別侮辱人家了,被那個生惡心的不行,我們班班草還被堵過呢。]
“……”
聊著聊著,話題又歪到了傅云瑞和時暮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事兒上,最后還有人拿出了時暮的殺馬特造型圖和學霸時暮對比,狠狠將之辱嘲笑了一番,顯然在一中眼里,那個消失的時暮是他們閑來取樂的東西。話題越來越歪,發帖人覺得沒啥意思,棄帖沒再出現了。
Advertisement
同樣熱鬧的還有英南學校論壇,考試績公布后的晚上,一個主題為[415的你為何如此特別]的帖子發布,不用想都知道這是嘲周植的。
夜融洽,415的幾人各忙各的,周植一派淡然從容的架勢,毫沒有考了倒數第一名的慌張,他正在看時暮的滿分數學卷,對著那秀麗的筆跡不住嘆,同樣都是人,同樣睡一間房,同樣吃的食堂飯,差距怎麼這麼大呢?
周植忍不住發出了疑問,“暮哥你不會是穿越過來的吧?你這也太牛了,你以后是不是要去上斯坦福啊?”
時暮手上一僵,不語。
周植不知自己道破了真相,持續嘆:“太牛了,真的是太牛了,給我吃十斤豬腦我都考不出這種績。”
他占據了傅云深位置,年沉著臉過來,連人帶凳子的一腳踹飛,周植早已習慣,拍拍屁重新坐好。
正收拾床鋪的夏航一低頭看他:“你英語考了0分,就算瞎蒙也不至于吧?你怎麼考的呀?”
周植翹著二郎,嘆息聲:“別提了,考英語的時候我太困給睡著了,想著就瞇一會兒吧,結果醒來就卷了,沒事兒,就算睜眼我也瞎,零分就零分吧,績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品格。”
傅云深似笑非笑:“這話和你爸說去吧。”
周植一聽,臉瞬間沉下。
他家老頭是窮苦人出生的,沒錢念書,15歲就出來打工,能走到今天非常不易。可是就算有了常人沒人的財富,心里始終擰著一個疙瘩,他想讓周家出一個狀元宗耀祖,于是就把這個愿強加在了周植上,周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他就不是讀書的料,兩父子因為這個沒吵架。
如今他英語考了零分,各項科目都不及格,等老頭拿到績單,估計會氣死過去。
周植嘆了口氣,整個人都蔫兒了。
時暮看出他不開心,拍拍他的肩膀安:“大侄子你別不開心。”
周植抬了抬眼,看的很開:“沒不開心,怎麼著我也是個第一啊。”
時暮:“能考倒數第一也是你本事,像我,想考倒數第一都考不了。”
夏航一附耳過來:“你別刺激他了。”
時暮:“我說的是真的,天生績好也苦惱的,很想驗一下倒數的覺。”
周植耷拉著下,再也控制不住,哇的聲就哭了,握拳不住捶桌,“我爸會打死我的——!”
“算啦算啦,我們不是說好了嗎,考完試請客,我看就下周放假吧,你把地址給我,我先預約個位置。”
正逢暑假,聚餐慶祝的人一定很多,再說周植看中的一定不是什麼小餐廳,提前預定總是好的。
周植悶悶不樂拿起手機,把餐廳位置發給了時暮。
記好,又拍拍周植的腦袋,轉頭去定時間。
考完試的最后幾天也沒什麼事,放假前一天,每個班級都舉行了簡單的小活,十五班也不例外。
過完這個暑假就要升高三了,十五班的人相互都有些不舍,一年下來彼此都出了,再開學還不知分哪個班呢,于是同學們都在班會上互送了禮。
傅云深向來對這種活沒什麼,他趴在書桌上,也不知是睡著還是在刻意逃避。
時暮桌上有已經堆了不的信封和禮盒子,朝后桌的傅云深看了眼后,抿抿斂會了視線。
講臺上,劉老師過來做最后發言:“我們班的同學今年做的都非常不錯,馬上就要升高三了,再過一年就要高考了,我知道大家都家庭殷實,但我還是希大家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有一個明的前途。最后,希你們離校時注意安全,玩兒的時候也不要耽誤了學習,還有,一會兒記得來場拍班級照哦。”
話音落下,劉老師離開班級,十五班的人卻都沒有。
傅云深手指頭勾勾,這才慢悠悠從桌子上爬起來,他懶洋洋打了個哈欠后,拎著書包起,正要離開時,班長住了他。
猜你喜歡
-
完結72 章

終身妥協
“只有我不要的玩意兒,才會拿出來資源共享。” “安棠算個什麼東西?我會喜歡她?” “玩玩而已,當不得真。” 港城上流圈的人都知道,安棠深愛賀言郁,曾為他擋刀,差點丟了性命。 無論賀言郁怎麼對安棠,她看他的眼神永遠帶著愛意,熾熱而灼目。 * 賀言郁生日那晚。 圈內公子哥們起哄:“郁少,安小姐今年恐怕又費了不少心思給您準備禮物吧?真令人羨慕。” 他指尖夾著香煙,漫不經心:“都是些沒用的玩意兒,有什麼好羨慕的。” 賀言郁已經習慣踐踏安棠的真心,反正她愛他不可自拔,永遠都不會離開他。 然而—— 也就在這晚,安棠突然人間蒸發。 港城再無她的蹤跡。 * 安棠從小就有嚴重的心理疾病,溫淮之是她的解藥。 溫淮之重病昏迷后,她舊疾復發,絕望崩潰之際在港城遇到賀言郁。 那個男人有著一張跟溫淮之相同的臉。 從此,安棠飲鴆止渴,把賀言郁當做溫淮之的替身,借此來治療自己的心理疾病。 相戀三年,安棠的病得到控制。 某天,她接到溫淮之的電話。 “棠棠,哥哥想你了。” 安棠喜極而泣,連夜乘坐飛機回到英國。 * 安棠消失后,賀言郁徹底慌了,發瘋似的找她。 結果,兩人相逢卻是在葬禮上。 身穿黑裙,胸前戴著白花的安棠,雙眼空洞,仿佛丟了魂。 那時賀言郁才知道,他們是青梅竹馬,彼此深愛。 而他,只不過是溫淮之的替身。 * 那天晚上大雨滂沱,賀言郁滿懷不甘和嫉妒,求著安棠不要離開他。 安棠用冰涼的指腹撫上他的臉。 “你不是淮之。”她笑,“但你可以一步步變成他。” “安棠會離開賀言郁,但絕不會離開溫淮之。” 那一刻,賀言郁從她眼里看到溫柔的殘忍。 后來,賀言郁活成了溫淮之。 他愛她,愛到甘愿變成情敵的模樣。 * 【排雷】 雷點都在文案里,追妻火葬場地獄級 男主前期又渣又狗,后期top舔狗 女主有嚴重心理疾病,但是會就醫治療,看立意
22.1萬字8 26921 -
完結179 章

掌中春色
陸執光風霽月,是天子近臣,寧國公獨子。 寧國公摯友戰死沙場,愛女無依無靠,被國公爺收留。 國公爺痛哭流涕,對外揚言定會視如己出,好生照顧。 小姑娘剛來那年乳臭未乾,傻乎乎的,還帶着稚氣,陸執看不上,沒瞧她第二眼。 不想到幾年後再見,人出落得清婉脫俗,便好似那天上的仙女一般,柳夭桃豔,魅惑人心。 陸執,越瞧心越癢癢...
25.7萬字8 14436 -
完結179 章

近我者甜
裴家小小姐裴恬週歲宴抓週時,承載着家族的殷切希望,周身圍了一圈的筆墨紙硯。 頂着衆人的期待目光,小小姐不動如山,兩隻眼睛笑如彎月,咿咿呀呀地看向前方的小少年,“要,要他。” 不遠處,年僅五歲的陸家小少爺咬碎口中的水果糖,怔在原地。 從此,陸池舟的整個青蔥時代,都背上了個小拖油瓶。 可後來,沒人再提這樁津津樂道了許多年的笑談。 原因無他,不合適。 二十五歲的陸池舟心思深沉,手段狠戾,乾脆利落地剷除異己,順利執掌整個陸氏。 而彼時的裴恬,依舊是裴家泡在蜜罐里長大的寶貝,最大的煩惱不過在於嗑的cp是假的。 所有人都極有默契地認定這倆be了,連裴恬也這麼認爲。 直到一次宴會,衆人看到,醉了酒的裴恬把陸池舟按在沙發上親。 而一向禁慾冷淡,等閒不能近身的陸池舟笑得像個妖孽,他指着自己的脣,緩聲誘哄:“親這兒。” 酒醒後的裴恬得知自己的罪行後,數了數身家,連夜逃跑,卻被陸池舟逮住。 男人笑容斯文,金絲邊眼鏡反射出薄涼的弧度:“想跑?不負責?”“怎麼負責?” 陸池舟指着被咬破的脣,低聲暗示:“白被你佔了這麼多年名分了?” 裴恬委屈地抽了抽鼻子,“你現在太貴了,我招不起。” 男人吻下來,嗓音低啞:“我可以倒貼。”
30.9萬字8 1904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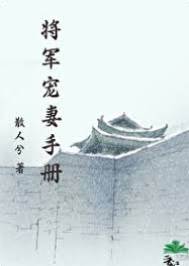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76 章

天鵝與荊棘
苦練四年的芭蕾舞劇即將演出,許嘉卻在登臺前被通知換角。 表演結束,她去找對方質問,沒想到撞進分手現場。 女演員哭花了妝,從許嘉身邊跑過。 她投以冷漠的一瞥,看向站在平臺中的男人。 邵宴清,豪門繼承人,手握大半的演藝資源,是圈內最堅固的靠山。 他與她像是雲和泥,一個如天邊月,一個如地上塵。 若錯過這個機會,她再無輕易翻身的可能。 “邵先生。” 許嘉走向他,從他手裏接過點燃的煙,將溼潤的菸嘴放入自己脣間,“要和我試一試嗎。” 邵宴清漠然地看向她,一言不發地提步離開。 許嘉以爲計劃失敗,三天後卻收到請函。 上面竟寫着:邀請您參加許嘉與邵宴清的婚禮。 — 許嘉非常明白,這場婚姻只是交易。 即使在感情最融洽時,她也沒有任何猶豫地選擇離開。 很快鬧出傳聞,說邵宴清爲一個女人着魔,新建公司,投資舞團,費勁心力只爲挽回她的芳心。 許嘉對此不以爲意,回到家門口卻是愣住。 一道高挑的身影守在門前,腦袋低垂,肩膀處覆有寒霜。 邵宴清的眼睛佈滿血絲,顫抖地攥住她的手,咬牙質問:“許嘉,你都沒有心嗎?” 許嘉尚未回答,已被他抵至牆邊。 邵宴清摟住她的腰,冰冷的脣覆在她的耳畔,似警告又似祈求:“許嘉,說你愛我。”
25.8萬字8 195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