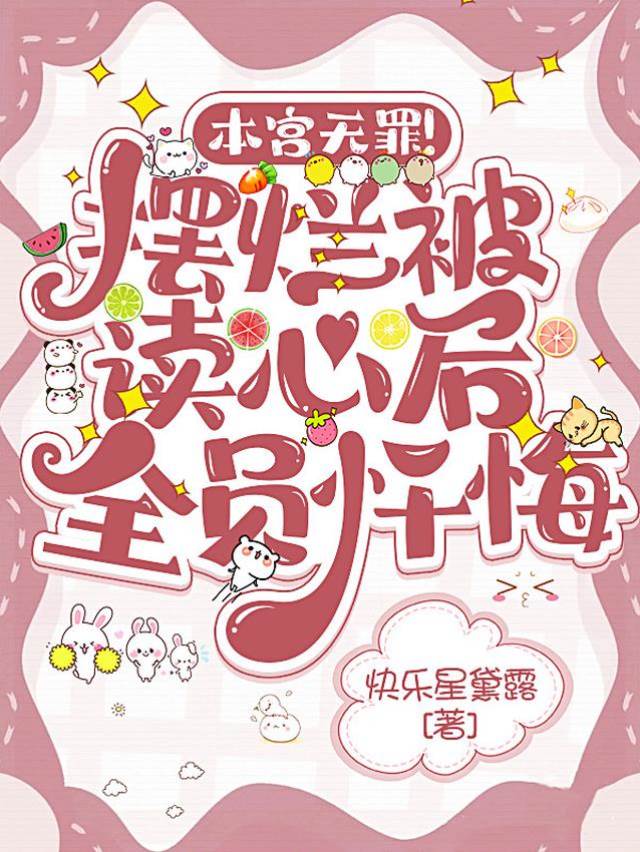《正妻不如妾ll》 二十九 曾同你相愛過
灰黑雲幕像浸著水的舊棉絮,漉漉,沉甸甸,直頭頂,直沖心頭。
天黑濃,涼風呼嘯。
這座城市士兵林立,戒備森嚴,城門口嚴檢查進城者的警衛和路上匆匆神張,滿目憂愁趕路的行人。
一個神無波瀾的男子和他的小廝坐在一輛不起眼的黃包車上,到了城門口,小廝不著痕跡地四下環顧,然後暗暗嫻地塞給檢查進城者警衛一金條,就這樣他們混了城。
他刀薄頜,寬肩長臂,車他的軀顯得裡頭的地方極小,一車靜謐略染孤冷,忽而好似從靜思中清醒,趙鈞默後車窗外景飛過,明暗閃爍的面龐上,兩道眉非濃非纖似劍一般鬢角,瞳眸微瞇,薄在略沉悶的車啟口道出一句劃破了寂靜:
“怕死麼?”
“什麼?”車,鄭副同趙鈞默坐於後座,前面開車的是他們的線人。鄭副一時沒聽清,低問著。
他倒不惱,複又說了遍:“怕死麼?我們現下進了敵人的腹地,若是有幸能從中打破,若是不幸,極有可能被吞沒。”不同於字句的意思,語調卻極為漫不經心。
“仲安不怕死,先生難道會怕?”
鄭副語畢,側過臉,向穿著極為平常樸素的中山裝的趙鈞默,車窗閃過的景忽明忽暗,天不好,他瞧著趙鈞默的臉亦是忽青忽白。
本來是一路無話的,誰知趙鈞默竟開了口,鄭副素來知道他在行事前不喜言辭,頗緘默,卻不料如今問他這話。
他淡淡地回頭瞧鄭副,側邊角漾著淺淡的笑意,涼薄的溢滿了似笑非笑自嘲的意味。
“從前是不怕的,如今怕了,有些事我還未理清楚。”
聞言,鄭副心裡“咯噔”一下,不由自主記起那日劉管事來報,說是大太太生辰當晚可能會同先生一見,哪裡料得那日火沖天,只瞧得見蕭念梳那子梨花帶淚的模樣,哪裡看得見大太太的蹤影。
Advertisement
然,鄭副心底卻不知為何莫名繚繞著些許不安,如是那樣的畫面,那樣的對話大太太看進了眼裡聽見了眼裡,豈非真真是至大的刺激,他想著中院許會出事,又替自家主子多派了些人看守,料到半況皆無,此等形竟他愈加擔憂。
要告知自家主子大太太生辰那日的事嗎……
“那日大太太生辰,您……”
鄭副言又止,心下正艱難地組織起語句卻不料被趙鈞默當下毫不猶豫地接口道:“給的面,定是扔得幹淨吧?”趙鈞默角微勾,猶如了然於,話出了邊,眼底皆是莫名的涼意。
“噯……”鄭副倏地臉一變,間略似魚刺梗住。
話雖如此,但……本是有機會見面的,夫妻間有何事是不能坐下來談的,有何事是不能消融的?
他亦有妻子,極知夫妻間的問題從來都拖不得,一拖這關系就僵了。暗自思忖間,鄭副面變化得快,抿得死,待到啟口卻竟是極為平淡的勸誡:“您若是真的對蕭小姐了真格,便,便放了大太太罷。”
此話雖是為大太太好,實則是為了趙鈞默,鄭副能覺到自己心中約泛起的不安同忐忑。
話落,座下都微了一下,趙鈞默怔怔地回看他,眼眸深邃,瞳孔微,指關節在膝蓋上淺淺泛白,待到恍惚間回神過來,已是攥了拳。
車空氣剎那稀薄了幾分,鄭副一瞬不瞬地同趙鈞默對,眼裡盡是勸與擔憂,霎時,趙鈞默淡淡地苦笑起來,這一笑使得氣氛松弛了幾分,半晌,他終是啟口答道:“不瞞你說,這事我從未想過。”
“那便從今日開始想吧,先生,你理應知曉,大太太心中恐怕已無你了。”
Advertisement
話已說到這般田地,再難晦暗搪塞過去,鄭副索攤開說話,豈料趙鈞默也不氣,只是略略別開了眼,在車窗約反的剪影中,好似能見著他的眼眸裡有些許意味不明的東西,他的聲音似是第一次如此無力地從間飄出來,帶著低到暗的沙啞道:“一直是我趙某自欺欺人,是我不舍得。”
舍不得那人,還是舍不得在人生中同那人一起的年景?
鄭副抿了抿,話含在裡,眼看到了直系錢參謀長的府邸,這番話只得爛在了間。
“鄙人姓明,是錢參謀長舊識。”一抵達錢俊甫的府邸,趙鈞默便笑容可掬地遞上名片,平日裡極是孤僻冷的臉有些許緩和,約出幾分儒雅,他並未用真名,素來在外行的習慣皆是用明晰的姓氏,此番一開口已是深知習慣難改。
那侍從趕忙招呼道:“明先生,參謀長還未從指揮部回來,請您在書房稍等片刻。”
言畢,便趕吩咐了奉茶上來,禮遇極佳。
錢俊甫自軍事指揮部回來時已是傍晚,待到侍從報說有位同為黃埔學生的明先生在書房等待自己時,他心下一,眼皮微跳,卻已是不能不見。
“哪個混蛋放他進城的?!”眉頭蹙,此人無事不登三寶,此番親自來,定是沒有好事,錢俊甫暗自思忖一番,腦中嗡嗡作響,不免冷聲怒斥。
話落,這分明的興師問罪,皆未有人敢答,下一秒,錢俊甫倒是心平複了些,揮手苦笑道:“罷了罷了,誰能阻得了他進來。”
若是不讓他進城,恐怕到時他在報上多加修飾,等等炮火恐怕就到了眼前了。
“參謀長,是否讓狙擊手在外埋伏?”侍從低聲附在他耳邊道。
Advertisement
“狙擊手?你給老子一邊去!他這家夥既然來了便不是來同我打鬥的,我若是禮貌待他,還能討得好去,若是武力相待,恐怕明日這城便不在了。”
古語雲,兩國戰不斬來使,何況此人還是報局的第一把手,素來死在消息上的無辜將士從來不,亦不缺他一個。
“咳,咳……”輕咳幾聲,終是推門而進,關上書房門,錢俊甫方瞧見那人端端自然地坐在他的主座上,模樣同數年前差別不大只是涼薄更甚,仍舊是冷峻的眉眼,含著意味不明的笑意,此時此刻,他正拿著自己前幾日未來得及看完的《拿破侖傳》,待見他進來,那人沒有站起迎接,而是合上書本放置一旁,對他招手,菲薄的笑得淺淡有禮,朗聲道:“俊甫兄,許久不見,你坐。”
一時語塞,錢俊甫冷睨著這人極為自如的招待作,心下發冷,這可是他的地方!
未來及發作,只聽那人又翻開書本,徐徐念道:“……你有一天將遭遇的災禍是你某一段時間疏懶的報應。俊甫兄可認同這句話?”
“有話直言。我素來最不喜你這副皮笑若不笑的樣子,本就不笑,何必要給我笑?”錢俊甫大步重重落座,沒好氣地道。
趙鈞默亦不惱怒,只是笑容微滯,有些悵然的眼眸變得幽遠起來:“同窗幾年,如今再見都敵人了,你說這世間有何是永恒的?”
這一傷的問話,同樣直錢俊甫心裡,心下不免蕭瑟幾分,當年的好些老同學一起研究軍事,一起槍林彈雨,如今卻是立於不同立場,沒個統一,各為其主,不可不說殘酷。
“你我都明白,時過境遷的道理。”
時過境遷……
他心中忽而似被,角微微發笑,趙鈞默稍平複了幾秒,抬手為錢俊甫斟茶,複又說道:“你有一天將遭遇的災禍是你某一段時間疏懶的報應。俊甫兄,我便開門見山吧,據我所知,你頂頭上面那人的最待見的五姨太是你時的青梅吧,你瞧我這記,我還記得生了個兒子吧,據我所知極像你。”
Advertisement
“……趙、鈞、默!”
重重一拳猝不及防地落至趙鈞默的左臉上,角頓時便滲出了,他沒有拭,只是從懷中拿出手帕,那手帕繡著栩栩如生的月季,芬芳吐蕊,可見繡此手帕之人極是手巧心細,未有作,錢俊甫一把搶過,拿起佩槍直對著趙鈞默的眉心,冷聲道,“你要我如何?!你說!”
“俊甫兄,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我要如何,我不如何,我此番前來不過是給你幾條路選,一你可呆在這裡守著你的佳人和這個被眾人虎視眈眈的部隊,又整日擔心你與之事敗鬱鬱不得志;二只要你將可靠的報與我,我可保證盡量減你部下的傷亡,你亦可帶著和子遠走高飛,如何抉擇全在你。”
“你還說了一句,說不定我們全要死。”
“你知道,我素來不說話不留餘地。”聳聳肩,趙鈞默冷眸微瞇,角勾起。
錢俊甫額大笑,冷汗直流,卻是終究松垮了肩,雙手握拳撐住頭顱,閉目低聲回應道:“也罷,這個面子我便賣給你……默卿兄,呵,老錢是許久不曾這樣你了,我知曉的,你是不忍心我死,若不是你來,恐怕我不到那麼多條路可選。”
話落,連趙鈞默腔都湧起一酸,可面上依舊冷漠平淡,只抬手拍拍錢俊甫後背道:“別說了,別說了……”
……
趙公館。
這日天氣極好,未時,碧空如洗,天晴得似一張藍紙,幾片薄薄白雲,被曬化,隨風飄遊時不時消散無邊。
許芳胎得厲害,幾日都要醫生陪著,連連養了些時日,稍有些好轉,日頭並不毒辣,反而溫煦,許芳在庭院裡喝茶吃著下午點心,卻是同領著好幾個丫鬟的蕭念梳浩浩個正著,眼皮都不帶掀起,許芳自顧自地吃著,一盤骨瓷碟上的小點心芳香四溢,口甜而不膩,蕭念梳瞧著極是礙眼,尤其是見著許芳的肚子,恨不得一腳踹了。
“喲,大爺出去辦公務,你倒是也不擔心,竟然吃得這般好,我可是連連幾夜擔心得睡不著覺了。”慢悠悠地出聲,高昂而尖細的嗓音隨著蕭念梳搖著的團扇晃悠地響起。
“晚晚――莫跑!”
話音剛落,只聽聞一個沙啞低喝的聲音從遠傳來,眨眼間,一個白團便沖上了石桌,咬上一口彩可餐的小點心,許芳一驚嚇得刷白了臉,倒是幸好丫鬟後頭撐住了晃悠了一瞬的子。
蕭念梳定眼一看,更是恨極了這只貓,下意識啟口咒道:“又是這只畜生!怎麼還沒死!啊!你――”
話未落,一盤點心霎時扔得蕭念梳面上七七八八的,皆是膩味的蛋糕殘渣,氣得蕭念梳來不及面拭便發抖著直直指向明晰,咬著恨恨喊著:“你這個潑婦!”
“彼此。”明晰冷睨著蕭念梳,神極淡,言簡意賅,仿佛適才連盤子都砸過去的狠辣勁從未存在。
“小姐!”許芳下意識站起,連連喊了明晰一聲。
“二姨太,你怎這樣糊塗,你已是二姨太,怎好還喚‘小姐’!”後邊的丫鬟趕忙附在耳畔提醒道,卻是許芳沒聽進去,怔忡地盯著明晰未走遠的素影微微發愣。
“呵,皆是個沒良心的人,大爺出去這麼些天了,你們一個吃得好,一個同畜生玩得好,趙家有你們二人真是三生不幸。”
刻薄冷語,蕭念梳的話方落,豈料明晰未走遠,竟然轉了凝視看向蕭念梳,斑駁午日下,彎起角的笑容似笑非笑,神飄然,眸悠遠,嚨裡傳出不不慢喑啞的嗓音回道:“死了便死了罷,他若是真的死在了外頭……也算落得清靜。”
這般直接的話仿若只有方有資格說得出口,如此坦,這樣寡薄到了極致。
朦朧間,微雨驟降,徒留另兩人有些怔怔愕然得不能言語。
……
趙鈞默此番為策反各地軍閥與反叛部隊將員之事,奔波勞累不堪,竟一連過了好幾個月,回了趟局裡待到南京自己的府邸已是傍晚了,這連日下來,趙鈞默是生生瘦了一圈,眼窩深陷,頰骨突出,原本就廓分明的臉龐愈發顯得懾人而冷峻。
風塵僕僕回來,一眾家僕和家眷都迎在了門口,卻是那人從未出現,他冷眸在家眷中搜尋了一,角淡淡勾起了涼笑,是早知答案的。
“鈞默……”
蕭念梳上前眾目睽睽之下攀上他的頸項,撲進他的懷裡,那樣的低嗔的模樣引得旁人都心裡晃神漾。
懷中的溫度最是真實,然,一瞬間,眸中掠過一抹恍惚,趙鈞默耳畔倏地響起分別時錢俊甫問他:“默卿兄,我倒有一事未明,想向你請教。”
“但說無妨。”
“倒也不是什麼大事,只是好奇,為何每回皆用‘明’姓?”
話語一出,連他都不由怔忡,因他也未想過原由,半晌,他方低垂冷眸,複又淡淡地回道:“倒無特別之意……因我人娘家姓明。”
蕭念梳扣著他的窄腰,卻心下清明,見他意向闌珊,心中不免計較,眼神俱是怨懟。
到了家中到底是覺得好些,胃口都變好了些,回絕了好些人邀他的慶功宴,晚飯後,他只呆在了書房理滯留的公務,期間,劉管事向他大致說了些家中的況,好些日子,時間長要代的事亦多,本來無事聽著都有些心煩了,其實,這些本不是他該理的,以往,明晰還掌事時,他只管理政務便好,如今竟要聽這些瑣碎的事,不免心較煩雜,揮了揮手便示意劉管事可自行理。
見狀,劉管事趕忙道:“先生,最後尚有一事,我本是想單拎出來同您商談的,也罷,是這樣的,鮑裡斯醫生說二姨太胎位異常,恐要早產。”
猜你喜歡
-
完結287 章

重生后寒門醫妃被迫在京城搞內卷
她是侯府嫡女,本應在寵愛中長大,卻在出生時被仆人掉了包流落鄉間,養父母把她當牛馬,在榨干她最后的價值后,把她虐待致死。帶著空間重生歸來,她甩掉渣男,吊打白蓮花,脫離養父母,讓虐待她的人萬劫不復。當侯府接她回家時,她以為她終于可以感受到親情了,誰知侯府只是想讓她替養女嫁給瘸腿王爺。想讓她當瘸腿王妃?對不起,她醫術高明,轉身就治好了王爺的腿。想讓她在宮斗中活不過三集?不好意思,她勢力龐大,武力值爆表,反手就把對手拉下馬。想讓她和王爺沒有孩子?抱歉,王爺說他們要一胎二寶。可是,她想跟王爺說:“我們是...
53.3萬字8.18 50402 -
完結265 章
團寵公主:休夫后七個哥哥跪迎我回家
【團寵+公主+追妻火葬場+高甜+爽文】溫秋晚為報恩隱藏身份忍氣吞聲嫁給夜司宸三年,但男人分明不領情,還對她漠視不理。 她決定不裝了,她是公主,她攤牌了。 回鸞之日,三個哥哥跪迎,還有四個哥哥為她清掃天下,從此,她過上了大佬們毫無節操的寵妹生活。 一場相親宴,她綠了前相公。 夜司宸黑著臉拎著她的小馬甲,「自古沒有女人休夫,這休書我不同意」 七個哥哥怒目而視,「滾,秋秋是我們的」 八個男人搶的溫秋晚頭痛欲裂.....其實男人多了,也很苦惱呢!
42.6萬字8.18 12112 -
完結118 章

瑤臺春
鄭玉磬出身寒門,卻因貌美被採選美人的花鳥使相中 十五歲入宮選秀,新科進士對她一見傾心; 一首訴情的《鷓鴣天》令長安紙貴,今上爲全一段佳話,特此賜婚 孰料大殿驚鴻一瞥,竟令天子意動魂飛,遂君奪臣妻,將美人據爲己有 * 她做貴妃的第五年新君御極,奉遺詔,尊她爲皇太后 從天子外室到母儀天下的皇太后,她用了僅僅六年。 玉階之下,昔日良人已爲宰輔,君前奏對無一疏漏,唯獨對上皇太后的時候片刻失神 鄭玉磬幾欲落淚,袍袖下的手卻被一人死死攥住 新君龍章鳳姿,頭頂的十二玉旈微微晃動,面上含了溫和笑意 “太后若是再瞧他一眼,今夜送到長信宮的必然會是秦侍中的項上人頭。” * 劍指長安,新君做的第一件事情便是入錦樂宮探望這位名義上的母妃 她寵冠六宮,身世卻不清白,聽說是父皇從一位臣子手中強奪來的 父皇曾經當着衆臣的面說他,此子不類朕 但唯獨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倒是出奇地一致 * 朕見她第一面,就想將她搶到朕的身邊 總有一日,朕會叫她心甘情願
59.6萬字8 1810 -
連載50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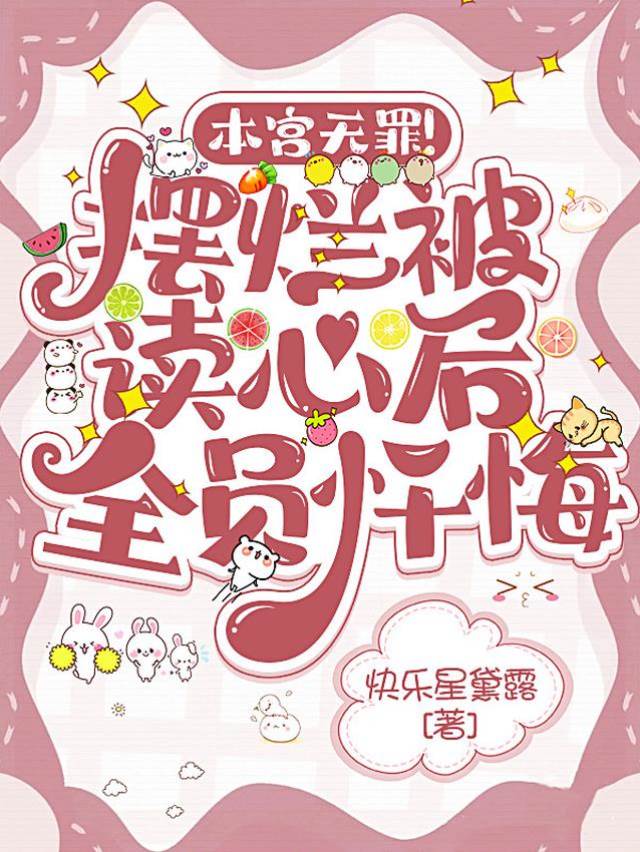
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
微風小說網提供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在線閱讀,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由快樂星黛露創作,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最新章節及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本宮無罪!擺爛被讀心後全員懺悔就上微風小說網。
85.5萬字8.18 3813 -
完結208 章

帝京有嬌嬌
聖旨賜婚虞幼蓮與江有朝時,京中所有人都覺得婚事雙方不搭。 一個是令國公府、簪纓世家千嬌萬寵長大的嬌嬌女,生得一副柔膚雪肌、眉眼如畫,叫人看了就想捧着哄着。 一個是寒門武舉出身,仗着軍功一躍成爲人上人的粗野將軍,曾一槍挑落敵軍數十,進京那日更是當街嚇哭兩歲稚兒。 江有朝本人也這樣認爲。 所以當令國公府遞來一張長長的嫁妝單子,上面列滿了各種珍奇寶物、時興首飾、綾羅綢緞的時候。 他也未置一辭。 只想着湊合將婚姻過下去,雙方相安無事便好。 直到春獵那日,那個紅脣雪膚,小臉如羊脂玉般瑩潤的嬌小姐,不小心撞進了他的懷裏。 江有朝大手一揮,將人穩穩接住。 對方盈盈拜謝,露出柔嫩細膩、不堪一握的脖頸,嬌矜又勾人。 江有朝狼狽鬆手。 ——在無人看到的角度裏,耳垂突然變得通紅。 * 京城衆人驚訝發現。 向來寡言冷語的江統領,婚後竟將自己明豔姝麗的妻子捧在了手心裏。 新婚第二日,他親自去金鑾殿前求了數箱羅綢錦緞,只爲小姑娘隨口說的一句牀榻太硌了; 生辰時放了滿城的孔明燈,只爲討她展顏一笑; 就連小姑娘鬧脾氣,也是他好聲好氣地哄着求着,生怕她受一丁點委屈。 衆人這才反應過來:那個令國公府千嬌萬寵長大的小姑娘,婚後居然比婚前還舒心自在。
33.5萬字8.18 11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