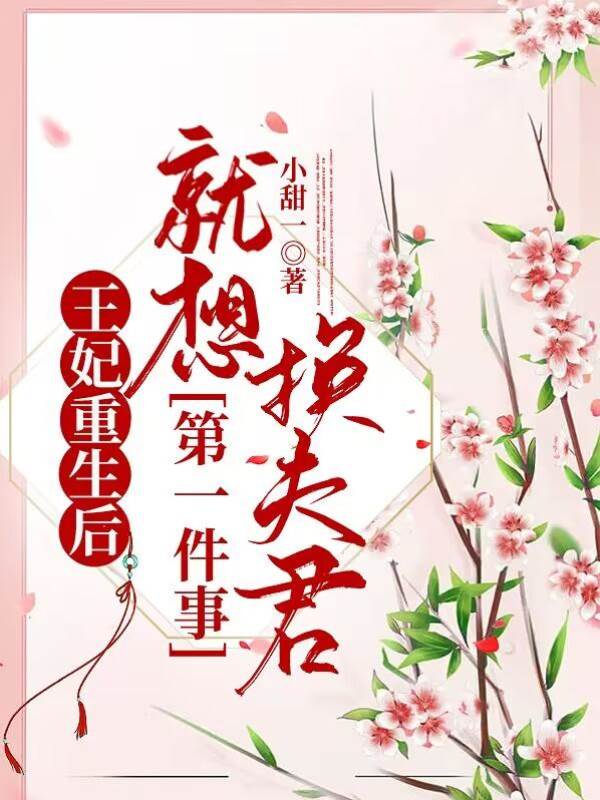《和離大作戰之庶女再嫁》 第五十八章 商會送來的芒果
“二小姐怎麼突然想起問慕云的事了呢?”徐伯有些疑的問道,又拿出一個茶杯給徐韶音倒了一杯茶水往面前推了推。
隨即仿佛想起了什麼,起走到后面的壁櫥那里手指在漆黑的空當里間索了半天,徐韶音居然驚訝的發現等他回來時手上居然放著兩個芒果。
“小姐,這是我那在西域行商的朋友帶回來的水果,名字我給忘了,不過味道是真的好,小姐嘗嘗吧。”
看徐伯藏的那麼嚴實,顯然這也是徐伯的心頭,看到這一幕,徐韶音無言的笑了笑,這個時代芒果說實話還是第一次看到,說不想吃那是假的,可是看到徐伯的樣子,頓了頓咽下口腔里剛剛分泌出來的口水,徐韶音聲道。
“原來是芒果啊,這東西我常吃,徐伯還是留著自己用吧。”
臉不紅心不跳的說完這些,徐韶音心中突然起了一個問題,如果說去西域行商的商人都可以弄到芒果的話,為什麼在大從來都沒有在世面上見到芒果,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府中其他人至在明面上還從未看到過誰吃過芒果,提過芒果,心中疑,徐韶音卻沒有就此忘記此行的目的,起把徐伯往壁櫥的方向推了推,笑著說道。
“這東西我常吃,你就自己留著吃吧,徐伯還是把慕云那個丫頭的戶籍登記給我吧。”
聽到徐韶音如此說,徐伯有些渾濁的目里多了一抹深意,頓了頓,再看徐韶音時分明眸子里帶了一些無奈和一些其他看不懂的東西,半天仿佛做了什麼決定一般,嘆息一聲,轉拿著那芒果又放回了壁櫥里,等到徐伯再坐下時,徐韶音發現他的神已經恢復了正常,已然沒有了方才的言又止。
Advertisement
“還是那句話二小姐怎麼突然想起要慕云那丫頭的戶籍登記呢?”
“我都說了啊,只是突然有些事想要知道所以就來問徐伯你了啊!徐伯你就給我吧。”說到最后,徐韶音一改往常的沉穩大氣,一撅,儼然用上了小孩子撒的口吻,一把拉住徐伯的胳膊左右搖晃,那架勢分明意思是如果你不給我就一直搖下去。
“二小姐你呀你呀!我還真拿你沒辦法!”無奈苦笑著搖搖頭,徐伯緩緩起,走向書桌后面,因為有書桌擋著,徐韶音看不到什麼,索將目收了回來,清冷的目再次對著房間里四周的東西打量了起來,只是這一打量卻讓看出了一些別的不同的地方。
正當心中暗暗沉思時,徐伯抱著一沓子卷宗走了過來,一把放在面前的桌子上,慈的說道。
“吶!這就是這安國侯府里所有婢的戶籍卷宗,小姐先等等吧老夫這就把慕云丫頭的戶籍找出來。”說完不等徐韶音回答,他整個人便了起來。
安國侯府里婢前前后后不下幾十名,可是放在桌子上的卷宗卻有一尺來高,徐韶音細長的眉眼淡淡掃了那卷宗一眼,卻沒有說話,只是手指著白瓷茶杯的邊沿在一旁細細的把玩。
時不時目放到面前認真查找的徐伯上,只是一瞥便又不經意間收了回來,時間一點一點過去了,徐韶音從頭到尾都維持著那個舉,沒有不耐煩,平靜如故。
好在沒有多久,徐伯便一臉驚喜的著一張薄薄的紙片從一尺高的卷宗后來將頭揚了出來,一把放在徐韶音的面前,含笑說道,“這就是慕云那丫頭的卷宗,二小姐好好的看看。”
看著眼前有些發黃的紙張,徐韶音心中一,沉聲問道。“這樣吧,在這里我也看不明白,若是拿回去有什麼不懂的地方我還能去問慕云那丫頭,所以徐伯我就先拿回去看了啊!”
Advertisement
說完眉眼彎彎一笑,拿了那卷宗,起就要離開,只是行快,徐伯的行顯然比更快,只是幾步便一把攔在了的前面,指著懷中的卷宗道。
“二小姐,這卷宗老爺一向是不許其他人翻閱的,讓二小姐看已經是通融了,二小姐如果真的想看不如就在這里看完再走吧,至于拿回去那是萬萬不行的。”
一聽這話,徐韶音眉眼冷了下來,想起方才看到的那些異常,定定的看了徐伯幾眼,臉上反而映出如花的嫣然淺笑,手牢牢的著卷宗,一把扶著桌子坐了下來道。
“那既然父親有令,我自然是會遵命的,那就聽徐伯的話,我在這里看完再走。”說到這里,徐韶音黑漆漆的眼珠子在眼眶里轉了轉,看著徐伯道。
“只是徐伯我這會有些想吃方才你的芒果了,我看那芒果不止一個,要不你給我一個吧。”
從小到大,徐立因為忙于政務,所以并沒有多時間陪伴徐韶音,又因為自己的母親只是一個妾室,為庶出小姐的徐韶音打小因為徐立的寵,所以奴婢們倒也不管怠慢。
可是終究還是十分孤獨,徐伯倒是常來陪玩耍,今天去的東街,當初就是徐伯帶去的,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徐韶音在徐立心目中的分量越來越重,同嫡母和庶妹之間的矛盾越來越重。
不知從幾何時開始居然忘了那個小時候一直陪伴著的老頭是何時開始淡出了的生活,只是在偶爾府中遇到時多了一抹恭敬的笑容。
“小姐,真的要吃嗎?”徐伯萬萬沒想到徐韶音會突然提起方才芒果的事,目深深的注視著徐韶音半天,沉聲問道。如果說方才還不確定的話,那麼這一刻徐韶音可以確定自己心中的猜想,當下揚起一抹燦爛的微笑重重點頭。
Advertisement
“好!”淡淡的應了一聲,徐伯將桌子上的卷宗整理好,臨走時再次深深看了徐韶音一眼,朝著壁櫥的方向走去,等到徐伯轉過,徐韶音的眉眼已然換上冷意,冷冷的瞅著眼前的老者,徐韶音心中不知是何滋味。
等到徐伯拿著一個不大的芒果走回來的時候,徐韶音面上笑如花仿佛方才那眼中如同千年不化的冰霜的人不是,看到芒果,徐韶音故作激的起一手拿著卷宗一把快速接了過來。
“多謝徐伯就知道徐伯對我還是像小時候一樣好。”
聞言徐伯的眼中升起一抹復雜的意味,深深看了徐韶音幾眼,緩緩挨著桌子坐下,徐伯房間里的桌子并沒有很大,可能是因為一個人吃飯的緣故,這桌子竟是比徐韶音房間里的梳妝臺還要小上三分,隔著不大的桌子徐韶音只覺得手下的桌子在微微抖,覺到面前鬢角已經有些發白,向來沉穩的老者如今就連呼吸也急促了幾分。
“謝謝徐伯,那我就先看了啊!徐伯卻是有事就自己去忙吧。”對著徐伯甜甜一笑,徐韶音拿起手中的卷宗看了起來。
安國侯府在朝中權勢并不很大,但是只要有權利的地方就一定有爭斗,為了防止那些對頭在自己的府邸中埋藏棋子,所以如果要從外面找丫鬟的話,那些牙婆必須是家清白,沒有不良記錄的。
不僅如此,每一次婢小廝的世況也要一一認真登記,這也是為了給那些可能會混進來做不好事的婢和小廝一個警告,如果們膽敢對安國侯府的人不利的話,只要做出來的話,那麼們的家人就沒有什麼好下場。
但是如果們好好干活的話,那麼自然待遇薪酬都是十分的厚的,若是遇到了脾氣好心底好的主子的話,等到他年滿多歲被放出去的也不是沒有的。
Advertisement
當然這個徐韶音還未見過,只是聽說在徐立父親那一輩倒是有過。
卷宗寫的十分詳細,不僅慕云的出生年月,還有籍貫那里,就連父母姓名,籍貫那里也是寫的清清楚楚,至于在為何到安國侯府里賣為婢一欄子里寫的也和徐韶音知道的沒有什麼不同。
家中太過貧窮,為了溫飽,父母將慕云給了牙婆,牙婆心也同這個可憐的小娃便把推薦給了那個時候因為自己出生而想要招聘婢的安國侯府,慕云自此進了安國侯府了自己邊一個不善言語的婢。
至于慕云這個名字,徐韶音遍了卷宗都沒有找到究竟是誰給起的這個名字,反正不是起的,而且等到能夠說話時慕云已經這個名字了。
雖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突然糾結于慕云這個名字,徐韶音卻不打算就此放過,所以挑眉看向徐伯輕聲問道,“徐伯,慕云那個丫頭是來了安國侯府時就已經有了名字,而且名字慕云的嗎?”
“二小姐說的不錯,那丫頭確實進了安國侯府時便那個名字,本來所有新來的小廝婢都必須讓新主子重新起名字的,可是老爺在聽了的名字后說了不錯,這名字便留了下來,小姐后來也沒有改,所以慕云這個名字就一直留了下來。”捋了捋胡子,徐伯沉聲說道。
“可是我看這里分明寫著慕云的雙親只是普通的莊稼人,大字不識,怎麼會給慕云起這樣一個十分有詩意的名字呢?”指著父母雙親況一欄,徐韶音再度問道。
“這個老夫倒不清楚,想來可能是因為疼,所以請了教書先生起的名字也猶未可知啊!”
顯然知道自己這句話有些站不住腳,慕云的父母之所以把賣掉就是因為家里窮,試問一個溫飽都保證不了要去賣兒的人又怎麼可能會想著去找教書先生只為了給自己兒起一個好名字呢!這怎麼都說不通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698 章

農門凰女
他是村裡最年輕的秀才,娶她進門,疼她、寵她、教她做一個無所畏懼的悍妻,對付糾纏不清的極品親戚。
310.4萬字8 83298 -
完結852 章

我見探花多嬌媚
靖寶有三個愿望:一:守住大房的家產;二:進國子監,中探花,光宗耀祖;三: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顧大人也有三個愿望:一:幫某人守住家產;二:幫某人中探花;三:幫某人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
146.8萬字8 32660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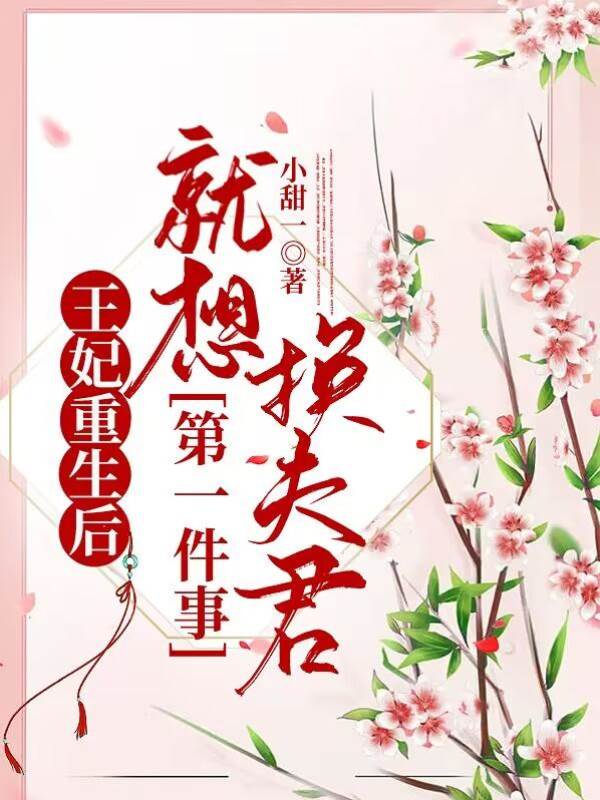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
完結105 章

夫君他竟然
沈訴訴夢見未來,差點被自己的夢嚇死。 她將會被送入宮中,因爲被寵壞,腦子不太好,她在宮鬥裏被陷害得死去活來。 後來她就黑化了,手撕貴妃腳踩原皇后成爲宮鬥冠軍。 但那有什麼用呢? 後來皇帝統治被推翻,她只當了三天皇后。 最後她死於戰火之中,三十歲都沒活過。 驚醒過來的沈訴訴馬上跑路,不進宮,死也不進宮! 她的縣令爹告訴沈訴訴,你生得好看,不嫁人遲早要入宮。 沈訴訴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邊那個沉默寡言的侍衛不錯。 這侍衛長得帥身材好,還失憶了,看起來就很好拿捏。 之前沈訴訴機緣巧合把他救下,是他報恩的時候了。 沈訴訴和帥氣侍衛商量着要不咱倆搭夥假成親算了。 侍衛烏黑深邃的眼眸盯着她說了聲好。 沈訴訴下嫁府中侍衛,成爲坊間一大笑談。 她本人倒是不在意這些,畢竟她家侍衛夫君話少還聽話。 沈訴訴性子驕縱,壞事沒少幹,上房揭別人家瓦時,墊腳的石頭都是他搬來的。 她身子弱,時常手腳冰涼,她把他當暖爐,抱着睡一整夜,他也毫無怨言。 她要吃城西的熱乎糕點,他施展常人所不能及的絕佳輕功,回來的時候糕點還是燙的。 沈訴訴過了幾年快活日子,後來江南有禍事起,叛軍要推翻朝廷。 這也在沈訴訴的預料之中,她準備叫上自己老爹和夫君一起跑路。 但她的侍衛夫君不見蹤影,沈訴訴氣得邊跑邊罵他。 她一路跑,後面叛軍隊伍一路追,沈訴訴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他們啥了。 最後她沒能跑過,被亂軍包圍。 爲首鐵騎之上,銀甲的將軍朝她伸出手,將她抱到馬上。 沈訴訴麻了,因爲該死的……這個叛軍首領就是她夫君。 難怪追殺(劃掉)了她一路。
15.5萬字8 21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