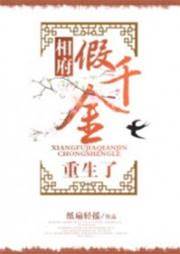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被庶妹替嫁后》 第16章 第十六章
新绦的柳葉將褪去綠的,韓祎坐在涼亭中,影的覆面自上起,一大半都罩在沉暗的影中。
他被風吹起的柳葉隨斑駁的影子在梨白的袖上浮,半分不曾為午時燥熱的天氣所影響。
郁桃站在原地,一不的瞧著。是有心走過去,只是找不著合適的理由。
許是注視的目太過炙熱,亭子里的人有所應,忽的抬眼,不咸不淡的一,那抹影投眸中時,眼睫掀起微不可查的停頓。
郁桃眼睛亮起來,帶著明的日,飽鼓舞的抬手招了招,一顆小犬齒樂得出半個小尖角。
“世子哥哥!”
的招呼恰到好,不至于太過魯莽擾了這一片的安寧,但也不至于太過小聲,讓亭子的人聽不見。
至目前從韓祎的反應來看,他是聽見了的。
只需要保持熱與微笑,然后等著他回以反應,邀請進涼亭。
但是,忘了那是韓祎,不是尋常人。
韓祎看向的時間甚至還沒有在半空中停留的時間長,不能說沒有反應,只能說是毫無反應,他便重新看回手中的件。
以郁桃的目力所及,那是一個烏木雕筑的娃娃,大腦袋小子,到圓滾滾的。
只能用一個字概括—— 丑。
但是卻吸引了韓祎的全部注意力,哪怕今天郁桃如此心打扮。
就這?
并不服氣。
郁桃手在袖中,片刻扭著咳了咳,一手拿著手帕掩在頭上,聲道:“哎呀,這里好曬呀!”
的余瞧見韓祎將娃娃放置在石桌上,抬手取了樣東西,很快,視線又重新投注回的上。
“今天怎麼這麼熱呀。”郁桃著帕子拭額頭的并不存在的汗水,“曬得我都快中暑了。”
Advertisement
韓祎就那麼淡淡的看著,薄暴在盛中,是不同于本冷淡的殷紅澤。
“世子哥哥。”把控著時機開口,“你看外面這麼熱,我子不好,曬不了太。”
踩著特意扭出來的曼妙步伐,往那邊挪,“世子哥哥,我能不能去涼亭和你一起坐坐呀?”
特意咬重了‘一起’兩字。
果不然,韓祎的目挪到了臉上,靜靜地打量半響。
“不能。”
?
郁桃歪了歪頭,你以為我是在問你意見嗎?我只是通知你罷了。
提起子,歡快道:“好的呢,世子哥哥,既然你同意了,那我馬上過來。”
......
然而踏進了涼亭中,才發現里面只有兩張石凳,其一被韓祎占著,其二被韓祎那兩本書冊子占著,
看看石凳,又看看韓祎,若是他不吱聲,石凳上的東西便無人敢挪。
當然除了郁桃。
嗐,兩本書嘛。
郁桃輕輕松松拿起來,‘啪’一聲將一本丟在石桌上,作自如的坐下,甚至為了好看,特意扭著和子,右手撐著下,錯婀娜的姿態,順手將另一本拿在手中慢悠悠的扇著風。
韓祎在其旁,拿著刻刀,在木雕娃娃的臉上一筆一劃。
直到落下來的書掀起陣風浪,旁余的視線里出現一只膩白的手,同時湊近的還有一張小臉和散落在臉頰邊的細,似有似無的桃子清香撲面。
的衫是日下的湖面所漾出的波紋與天際的流云,所有的走線都順著形而下,別出心裁的勾勒出細的腰與匍匐在石桌上快要沁出水的飽滿。
韓祎手下微重,木雕軋出一道深痕。
郁桃手中的書頁扇,薄脆的紙面聲響中牽連著空氣中的燥意。
Advertisement
他兀然側頭,“你很熱嗎?”
“啊?”郁桃眨眼向他,對這突如其來的關心有些錯不及防。
眼睛轉了一圈溜回去,抿甜笑:“是很熱呀。”
韓祎沒說話。
郁桃默默在心里細數著他的眼睫,一面看過深邃的眉眼和高的鼻梁,一熱氣沖頭。
“你知道為什麼這麼熱嘛?”
韓祎面無表的看著。
郁桃歪頭傾向手臂,眨了眨眼睛,笑容更加甜:“因為看見世子哥哥,我就覺得心里很熱呀。”
韓祎漠然的挲著刻刀,“看見我?”
“嗯,沒錯,就是看見你。”郁桃點點頭。
湖邊涼風襲面,四面樹木的葉子沙沙作響,日傾斜,照涼亭中。
韓祎斂目微盻,目比他手中的刻刀還要琢磨人。
兩人面面相對,往前湊了湊,看著那張臉補充道——
“熱到□□焚。”說。
那雙幽黑的雙眸倏然一。半響,他嗤一聲笑,袖手起離開此地。
......
這就走了?
我說錯了什麼嗎?
郁桃眨了眨眼睛,沒怎麼想明白,到底又是什麼話得罪了或者是嚇跑了他。
但是毫不猶豫的跟了上去,也不畏懼這會兒日頭比剛才還要大,丟下翹楚和拾已,聲喊道:“——世子哥哥。”
韓祎其實走的不快,若不是郁桃了解此人絕決義的個,都要誤會他是不是故意放慢滿了步調在等自己。
廊上安安靜靜,輕的燈籠隨著風還有幾分歲月靜好的意味。
郁桃穿過他后的隨從,落于半步的位置,才停下來,面帶笑容:“你怎麼突然走了呀,差點追不上你。”
不等韓祎回答,彎著眼睛,笑瞇瞇問:“世子哥哥是不是擔心我跟不上,所以走的這麼慢呀?”
Advertisement
韓祎垂眸,目從臉上輕輕掠過。
他看著,漸漸停下腳步來。
覺得他應該是想要說什麼,心口莫名張的跳起來。
“姐姐。”
一道輕的聲音傳來,郁桃轉頭看見郁苒站在拐角,頭頂罩著一把傘,而撐傘的正是段岐生。
郁苒目微閃,像是才看見人一般,朝韓祎福,“韓世子。”
韓祎掀了掀眼瞼,點了下頭。
晦氣!
郁桃了手臂,想要溜走,卻突然又被住。
“姐姐。”
在心中翻了個大白眼,轉過,懶洋洋道:“干嘛?”
郁苒一手捂在口,看了眼韓祎,又看了眼,言又止:“姐姐吃夠沒?那頭宴席還沒撤下來,要是了還能回去吃兩口。將才我在桌上看到姐姐著急出去,像是也沒吃什麼東西......”
郁桃扯著,“勞你費心,時刻盯著我。”
“姐姐誤會了,我只是關心姐姐,沒有別的意思。”郁苒楚楚可憐的站在傘下,弱的似能被風刮倒。
“哦。”郁桃深吸一口氣,微笑:“和我有關系?”
“姐姐......”郁苒的眼中含著淚水,“你是不是還在怪我...如果是為了那件事,我從前那些無知的話,現在岐生哥哥也在這里,只要你愿意原諒我們......”
“郁苒。”郁桃看著惺惺作態的模樣,忍無可忍的打斷,“如果你吃飽了,那我勸你早些喊個府醫來瞧瞧。”
郁苒的淚水尤掛在眼睫上,聽見說府醫二字,明顯往后退了兩步,靠在段岐生前,一手張的在小腹前。
郁桃抬起下,看著著致朱釵的腦袋道:“——瞧瞧你的腦子,會不會傳到肚中的孩子。”
Advertisement
說完,瞥向撐傘的段岐生,“哦,忘了還有你。”
“郁桃!”段岐生臉變了又變。
郁桃笑看向他:“你是不是忘了該如何稱呼我?”
段岐生頓時啞口無言。
郁桃看著傘下二人,前者虛與委蛇后者瘠人己,絕配,越看越覺得絕配,甚至離開時忍不住抬手道一聲‘百年好合,早生貴子’。
而也未曾看到留下的兩人臉上的神數十來回,極其彩。
這一回博弈,郁桃再次完勝,走在廊上的步伐都要輕快許多,但很快想起個被忽視了有一會兒的,也是方才作壁上觀的人。
的心了一下,忍不住用手捂住。
錯了...
剛才那麼好的時機,自己應該裝裝弱的。
嗚嗚嗚,我為什麼那麼兇猛,表現得那麼強勢。
心重復著一萬遍咬手帕痛哭,嗚...都怪郁苒,每次都來擊怒我。
想到郁苒那幾句‘趕著出去,沒吃幾口’,還是想要微微的掙扎一下,希挽救自己大家閨秀的形象。
斟酌再三,輕聲喊:“韓...韓偉。”
前面的腳步停頓,但不知為何郁桃從這個停下的作到轉,都能觀察出主人心的不悅。
也不能算作是不悅,因為韓祎的神只是淡然的,等著說話。
郁桃低著頭,鞋履在地上輕磨,“我雖然時常煩擾你,但并非像郁苒說的那般,飯也不吃便故意來尋你。”
畢竟誰也不能耽誤我吃飯。
“我平日說話也很溫,和妹妹關系也十分好,我們相親相,在于郁府長大,我恨不得將自己最好的一切給。”
并不是,我恨不得親手把給咔嚓掉。
了眼睛,眨著兩顆淚珠,在抬頭的瞬間出楚楚人的神:“世子哥哥,你要相信我。”
的眼睫纖長,瞳仁是亮的琥珀,眼尾微微勾著,紅的眼眶。
其實并不是郁桃所設想的模樣,反而帶著難以言說的勾人的味道。
“相信我,好不好嘛…世子哥哥。”
“嗯。”韓祎的回答慢了一瞬,說話的同時他提步往前。
狗男人,敷衍我!
郁桃再一次小步追上去,突然想起再到郁苒之前,狗男人是不是想要說什麼?
“欸?”湊過去,眨著好奇的目:“世子哥哥,你那時候是不是想要問什麼啊?”
韓祎掀了掀:“沒有。”
“真的嗎?”才不信,明明人都停下來,眼睛看著,話都到邊了。
絮絮叨叨的回憶:“我問你是不是特意慢慢走等我,然后你停下來了,對對對,就是這個時候突然遇到郁苒了嘛,原本你想要說什麼,你不記得了嗎?不可能呀,這點時間你都不記得了呀?”
韓祎突然停下來。
郁桃笑意盈盈的看著他,聲道:“是不是我替世子哥哥回憶一番,又想起來了呀?”
所有的想法都寫在臉上。想要得到的,不停得寸進尺的試探,以及自以為掩飾的極好實則拙劣的手段。
他低著頭,帶著那麼點心不在焉的意味,像是在看后又像是在看。
“郁苒是你一母同胞的妹妹?”他問。
?
郁桃看著他,緩緩冒出疑問。
我關心你,你卻關心我的妹妹?
可人的笑容僵化在臉上,角不聲的了,一個簡單的句子在腦中消化了半天。
沒有聽錯的并且十分確定,韓祎詢問的確實是的妹妹 —— 郁苒。
于是,出了一個更加甜膩的笑容,著更為嗲的聲音。
“世子哥哥,你猜猜呀。”
作者有話說:
猜你喜歡
-
完結421 章

名門醫女
齊悅一腳跌進了陌生時空 梳著婦人頭,不見丈夫麵 獨居彆院,冷鍋冷灶冷眼 開什麼玩笑 既然我是這家中的大婦 自然我說了算 好吃好喝好住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再跟我鬥再跟我鬥 外科聖手嚇死你們
118.3萬字8.09 141181 -
完結691 章

錦鯉農女有慧眼
白富美學霸花顏穿越成農女,獲得一雙洞悉過去,預知未來的慧眼。果斷脫離極品家人,擒獲書生小奶狗一枚,從此成為“護夫寶”。她靠實力成團寵,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其實,花顏隻想過普通人的生活,奈何被寵成富可敵國、權傾朝野的女霸王!
122.5萬字8 28006 -
完結2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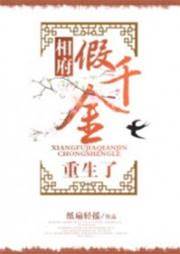
相府假千金重生了
蘇靜雲本是農家女,卻陰差陽錯成了相府千金,身世大白之後,她本欲離開,卻被留在相府當了養女。 奈何,真千金容不下她。 原本寵愛她的長輩們不知不覺疏遠了她,青梅竹馬的未婚夫婿也上門退了親。 到最後,她還被設計送給以殘暴聞名的七皇子,落得個悲慘下場。 重來一世,蘇靜雲在真千金回相府之後果斷辭行,回到那山清水秀之地,安心侍養嫡親的家人,過安穩的小日子。 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傳聞六皇子生而不足,體弱多病,冷情冷性,最終惹惱了皇帝,失了寵愛,被打發出了京城。 正在青山綠水中養病的六皇子:這小丫頭略眼熟? 內容標簽: 種田文 重生 甜文 爽文 搜尋關鍵字:主角:蘇靜雲 ┃ 配角: ┃ 其它: 一句話簡介:惹不起,我躲還不行麼? 立意:
39.4萬字8 30734 -
完結451 章

農家俏媳山裡漢
賀思思眼睛一閉,一睜,就成了杏花村待嫁的小村姑。 嫁妝?不存在! 親戚?都是極品! 左手賺銀子發家致富,右手虐渣渣一身輕鬆,順便再拋個飛眼,撩一撩哪哪都合她眼緣的糙漢子。 啥?他就是用一頭野豬把她聘回家的未婚夫?
82.8萬字8.18 118142 -
完結137 章

招魂
-落魄的閨閣小姐X死去的少年將軍-從五陵年少到叛國佞臣,徐鶴雪一生之罪惡罄竹難書。即便他已服罪身死十五年,大齊市井之間也仍有人談論他的舊聞,唾棄他的惡行。倪素從沒想過,徐鶴雪死去的第十五年,她會在茫茫雪野裡遇見他。沒有傳聞中那般凶神惡煞,更不是身長數丈,青面獠牙。他身上穿著她方才燒成灰燼的那件玄黑氅衣,提著一盞孤燈,風不動衣,雪不落肩,赤足走到她的面前:“你是誰?”倪素無數次後悔,如果早知那件衣裳是給徐鶴雪的,她一定不會燃起那盆火。可是後來,兄長失踪,宅田被佔,倪素跌落塵泥,最為狼狽不堪之時,身邊也只有孤魂徐鶴雪相伴。 伴她咬牙從泥濘里站起身,挺直腰,尋兄長,討公道。伴她雨雪,冬與春。倪素心願得償,與徐鶴雪分道揚鑣的那日,她身披嫁衣將要嫁給一位家世,姿儀,氣度都很好的求娶者。然而當夜,孤魂徐鶴雪坐在滿是霜華的樹蔭裡,看見那個一身紅的姑娘抱了滿懷的香燭不畏風雪跑來。“不成親了?”“要的。”徐鶴雪繃緊下頜,側過臉不欲再與她說話。然而樹下的姑娘仰望著他,沾了滿鬢雪水:“徐鶴雪,我有很多香燭,我可以養你很久,也不懼人鬼殊途,我們就如此一生,好不好?”——寒衣招魂,共我一生。 是救贖文,he。
50.1萬字8 227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