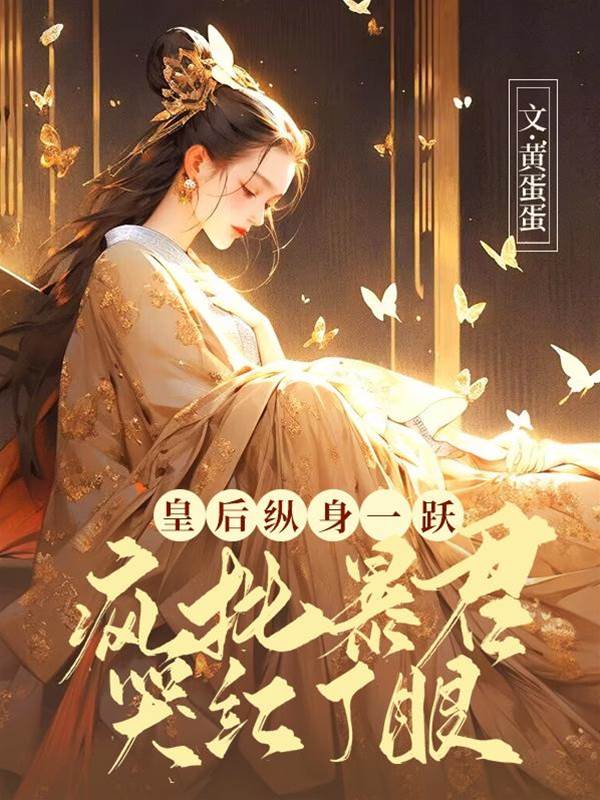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被庶妹替嫁后》 第60章 第六十章
直到第二日, 棋霜都未回院中。
梳洗時來伺候的是郁苒帶去段家的陪嫁丫鬟沁水,一向不喜歡這個沁水,模樣雖不大出挑, 卻盛雪,姿妖嬈。
郁苒隔著銅鏡看見沁水前遮不住的起伏, 心里一陣煩躁。
拂開沁水的手, 問:“棋霜呢, 讓來伺候。”
沁水俯首道:“早晨奴婢去喚棋霜姐姐,見房中沒有人, 以為是出去了。”
郁苒孕期里忘也大,才想起昨夜里一個人渾渾噩噩從外院回來, 邊不曾有棋霜在......
心里咯噔一跳, 猛地站起往外走。
院子里還是靜悄悄的, 人將踏出月門, 看見門口錢媽媽笑的一張臉,像是在此等了許久。
“段夫人。”
郁苒了袖口, 才發現柱子有些抖,出點兒笑, 一手上腹前的隆起,朝錢媽媽頷首。
錢媽媽眼睛淺淺略過蓋在腹前的那只手, 嗤出點笑, “咱們夫人吩咐, 府上屋子小,容不下大佛,還請段家兩位夫人趁天早些回去。”
“這是哪里的話。”郁苒強撐著笑容, “我還未向母親拜謝......”
錢媽媽打斷, “段夫人怕是不明白, 咱們夫人和你可是毫無干系,若要拜謝,那也應當去叩謝老爺才對。”
說完,轉向旁幾個腰膀圓的婆子道:“你們幾個就在此候著段家來的客人,等們行裝拾蹉齊整,便送人出門,可別等到中午大日頭,郁府可不留人午膳。”
婆子都呵腰稱是,虎視眈眈的立在月門前。
錢媽媽轉離去,也不管段家那位楊氏在里頭咒天罵地,郁苒在門口咬牙切齒。
Advertisement
郁府要敬三日的八字庚帖,早晨請將庚帖送去普化寺,得了大師一個‘宜’字,鄭氏聽聞消息,初時高興,待庚帖用一碗在廚房照頭,又覺得心里一陣愁緒。
“姑娘大了。”鄭氏搖頭道:“留不住了。”
錢媽媽勸:“這位世子奴婢瞧著,都覺得極好,大小姐有如此歸宿,夫人合該放心了。”
鄭氏這兩三日都未再見客,而是開了庫房,親自在一旁盤點件。
郁桃不知道母親在忙些什麼,偶爾去看一眼,忍不住問:“您這是在做什麼呢?”
鄭氏不理,開口問的卻是:“你與那韓世子是如何認識的?”
郁桃直起,支支吾吾道:“什麼韓世子?”
“閆韓侯府世子。”鄭氏看一眼,用手帕拭手中一樽紅玉雕,“閆韓侯府上門有些日子,從前阿娘聽你滿閆韓侯府,只當是小丫頭的玩笑話,現在想來也是有跡可循,你瞞著阿娘那些,我也不想去探知,只問一句,閆韓侯府提親,你覺得如何?”
閆韓侯府提親?
郁桃很是驚訝,驀然想起上一次送小郡主出去,在馬車跟前韓祎那幾句話的意思。
原來是這個意思?
一時郁桃卻覺得心中糟糟,像一團繩線埋在一起,不解與訝異互相牽扯。
待郁桃勉強鎮定,看向鄭氏,才發現母親神淡淡的,和方才的語氣一樣,也聽不出幾分脾氣,只是知母莫若,也曉得這是慪氣的意思。
日頭金燦燦,母間一時沉默,郁桃垂首立著,小聲道:“原是兒糊涂,瞎鬧了一陣清醒過來,只是沒想到世子前些時候尋過來,說了一些聽不懂的話,還請阿娘放心,兒雖冒失,但從未越矩。”
Advertisement
鄭氏道:“我雖對你無甚要求,但若是你做出像郁苒那樣的事,這門婚事如何我都是不準的。”
郁桃低下頭,“兒怎麼會學呢?”
鄭氏抬起頭,凝神兒的面。許久,手理了理額前的發,輕道:“阿娘只愿你這輩子平安喜樂,什麼侯府都不要。”
“都聽阿娘的。”乖巧道。
次日一早,門房婆子開了偏門,就被府外候著的車馬嚇了一大跳。
那滿臉堆笑的管事,婆子還記得,夢里糊涂的眼,“您這不是前些日子來過的?”
管事笑的極喜氣,從小廝手里接過個烏木系紅綢的匣子,順手遞過去一個紅封。
婆子一看,紅綢子定是喜事而啊,清醒了,‘唉喲’一聲,道:“您這客氣了。”
管事客氣道:“請務必將匣子給尊夫人,咱們在這兒等著信兒。”
婆子將紅封塞進袖口,小心翼翼接過匣子,喚上幾個丫鬟喜氣洋洋的往清風苑去了。
鄭氏才用過早膳,婆子院,錢媽媽正巧站在廊上,也不問是誰,從手里接過匣子,捧至額前緩緩送室,笑道:“當真是喜事臨來初照,跟夫人這裳一樣吉利。”
鄭氏解開紅綢子,匣蓋掀起,出里頭一張大紅鑲金的帖子,略略看,正是司天監測得‘大吉’‘相宜’的字眼。
這是來問郁家的意思。
,
鄭氏合上匣子,從案幾上拿出一樣系上紅綢的紅木匣子,到錢媽媽手中。
沒多久一眾婆子丫鬟圍著錢媽媽將匣子送出門,予管事。
錢媽媽笑道:“這便是郁家的意思。”
管事溢出滿臉笑容,翻上馬,跑得比來時更快。
.
郁桃一人在院中許多天,自打知道那件不得的事,心里始終忐忐忑忑,知道終是會來,卻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跟沸水里的茶葉似的上上下下。
Advertisement
翹楚不知道從何聽得消息,神神道:“聽外院婆子說,昨天閆韓侯府的老管事上門,請了一個系了紅綢的匣子回去,好些婆子丫鬟都得了紅封吶。”
郁桃逗著小貓,眼皮兒掀了掀。
此事知道,連那匣子都是母親當著面兒裝進去的。
翹楚見姑娘不得新鮮,在拾已的眼神里閉上,默默端著瓶出去換水。
晌午日頭正大,府里才午睡過,到且靜著,兀的幾聲鞭炮將人的瞌睡全部炸醒。
郁桃從書里抬起頭,蹙起眉問:“怎麼了?”
拾已真說出去看看,便看見翹楚風風火火從外頭跑進來,額頭還帶著晶瑩的汗珠,雙頰紅紅,著氣兒嚷道:“閆韓侯府來過禮了,閆韓侯府來過禮了,我看見那管事手里拎了好大一對雁。”
郁桃抬頭的作定住,怕是自己聽錯了,“誰來過禮了?”
翹楚指著外頭,興道:“閆韓侯府,姑娘快換裳出去看看,才唱禮單呢,奴婢瞧那擔子都排到胡同外,多府上開了門來看熱鬧,壯觀的。”
郁桃趕兒換了裳收拾出去,遠遠地看見那人一大紅直裰,袖口別著紅綢,堂亮的嗓門正唱,“海味十六式:鮑魚、蠔鼓、元貝、冬菇、海蝦、魷魚、海參、魚翅、魚肚等......”
先前所念不過是尋常富貴人家的件,待唱到后邊,越讓人忍不住咋舌,什麼黃金百斤,馬匹六十六,金銀茶筒,玉三十,良田......
系紅綢的雕花烏木擔子鱗次櫛比郁府門中,胡同巷子站滿了聞聲而來湊熱鬧的人。
郁桃將走出廊廡,鄭氏的眼風一掃過來,幾人便只敢站在抱漆大柱子后頭,不做聲的聽著。
Advertisement
彩禮唱完,郁桃的腳險些站麻。
翹楚捂著笑,“瞧這個聘禮,咱們姑爺可滿意咱們姑娘呢。”
拾已臉上掩不住笑意,卻說:“還在外頭,說話可省心些。”
唱禮之后,鄭氏便出了石階。
門外晃眼一過,郁桃瞧見韓祎立在鄭氏跟前,將聘書呈給母親。
平時見多了他穿深的裳,今日換了一件褚的寬袍,反而減了不冷清的意味,添了些郁桃從未見過的人氣兒。
他對長輩笑時的樣子,清雋而恭敬,郁桃也覺得很稀奇。
時至今日的一切,如夢似幻一般,總讓人覺得不大真實。
盯著人神游,也不知自己的眼神穿出去,韓祎已經無聲的看了幾回。
直到翹楚憋著笑,扯了下的袖子,郁桃暈乎乎回神,定睛之時,看清遠男人一雙黑眸掃來,猛地被燙了下。
抱漆大柱子后面幾道鬼鬼祟祟的影悄悄溜走。
鄭氏不知道這一遭,手里拿著聘書,只覺得沉重的很。
只因夾在其中一張黃綢,上寫著太皇太后親賜,短短幾行字,其力度可見。
只是這賜婚應當宣讀......鄭氏有些疑。
韓祎道:“宮中賜婚,原本應當宣讀,只是皇說給自家外孫兒點個婚,是尋常家事,不必走那些不必要的繁文縟節,這份賜婚能彰顯其珍重便是。”
這也說得過去,鄭氏凝神看,前頭無什麼要,只是這婚期......
韓祎道:“司天監算得,這一日是整年中最好的時候,又是風調雨順五谷登之日,萬事皆宜,十分難得。雖說了些,不過有宮中繡紡局在,一應都妥帖。”
宮中的繡紡局給自家兒做嫁,鄭氏是萬萬沒想過的。
無言半響,點點頭,便是應了。
還禮過后,鄭氏送走一行人,看著將府苑填的滿滿當當的彩禮和手上的禮單陷沉思。
不過三十日,將自己那幾座莊子宅子田地算上,似乎也只是勉強湊夠閆韓侯府彩禮中良田的末數。
當晚,郁桃逗著小貓,迎來了錢媽媽和后幾個挑著擔子的婆子。
翹楚‘唷’了聲道,“媽媽這是送什麼好東西來哩?”
錢媽媽含糊道:“夫人讓送來的,你們且看看,記得讓大姑娘認認真真的看看。”
翹楚和拾已吃力的將大箱籠搬室,郁桃抱著貓兒好奇的湊過去。
箱籠蓋子撐開,見著里頭是郁桃在清風軒里常用的那一并算盤。
再手翻一翻,底下全是厚厚一摞賬冊。若說從前,郁桃見過的賬冊頂多撥上四五顆算盤果兒,那這回母親送來的賬冊,怕是要將算盤撥全敲爛。
冊子第一面夾著張紙,是鄭氏的字跡——
閆韓侯府家大業大,為娘只能幫你到這兒了,好自為之。
猜你喜歡
-
連載1900 章

嫡女驚華
鳳驚華前世錯信渣男賤女,害的外祖滿門被殺,她生產之際被斬斷四肢,折磨致死!含恨而終,浴血重生,她是自黃泉爬出的惡鬼,要將前世所有害她之人拖入地獄!
194.9萬字8.18 337396 -
完結290 章

家有夫人兇又惡
傳聞朗月清風的韓相栽了,栽進那名鄉下長大,粗鄙不堪的將府大小姐手中… 自此相府每天都熱鬧,昨日剛點了隔壁尚書家,今日踹了那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 對此,韓相自始至終只有那淡淡一句話“夫人如此辛苦,此刻定是乏了,快些休息吧…” 某女聞言咽了口口水…腳下略慫的逃跑步伐邁的更大了…
26.6萬字8 10001 -
完結3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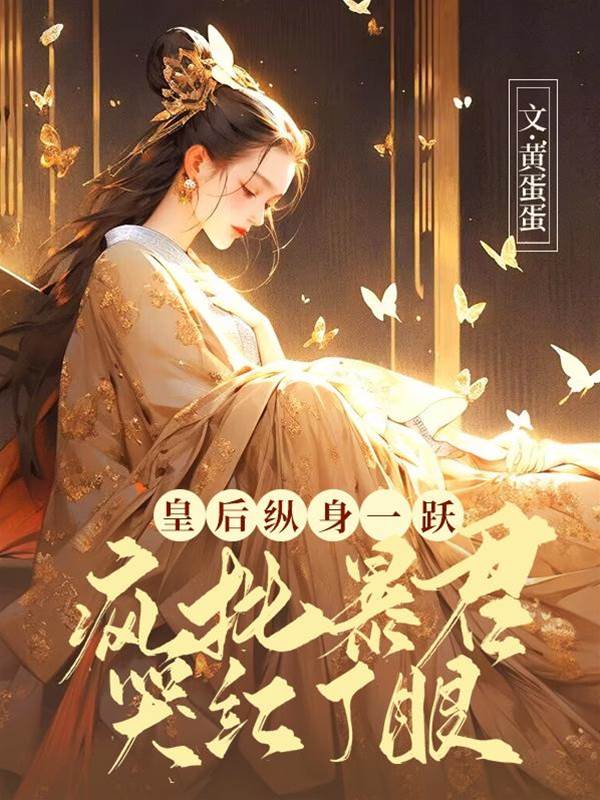
皇後縱身一躍,瘋批暴君哭紅了眼
【1v1,雙潔 宮鬥 爽文 追妻火葬場,女主人間清醒,所有人的白月光】孟棠是個溫婉大方的皇後,不爭不搶,一朵屹立在後宮的真白蓮,所有人都這麼覺得,暴君也這麼覺得。他納妃,她笑著恭喜並安排新妃侍寢。他送來補藥,她明知是避子藥卻乖順服下。他舊疾發作頭痛難忍,她用自己心頭血為引為他止痛。他問她:“你怎麼這麼好。”她麵上溫婉:“能為陛下分憂是臣妾榮幸。”直到叛軍攻城,她在城樓縱身一躍,以身殉城,平定叛亂。*刷滿暴君好感,孟棠死遁成功,功成身退。暴君抱著她的屍體,跪在地上哭紅了眼:“梓童,我錯了,你回來好不好?”孟棠看見這一幕,內心毫無波動,“虐嗎?我演的,真當世界上有那種無私奉獻不求回報的真白蓮啊。”
53.4萬字8.18 417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