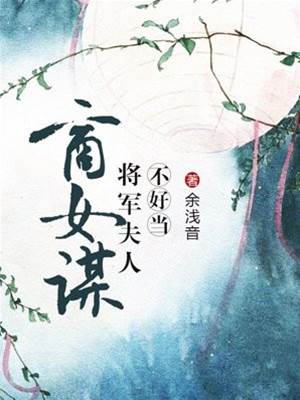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帝肆寵(臣妻)》 第15章 第十五章
蕭持在養心殿里來回走著,不時,張堯躬邁著步子進來,他停下腳步,轉頭問他:“如何,換了?”
聲音里有些急切。
張堯便笑笑:“應該是換了,喜禾姑姑開始特意拿了一套潁川上貢的蜀錦制縷金穿花云緞,可姜醫嫌那服太浮夸了,不肯穿,奴婢看著最近才拿進去的,是前不久榮昌公主挑中那款,水綠,低調!”
蕭持斂眉想了一會兒,手在掌心上敲著,半晌后對他道:“去跟榮昌公主問問,如要送子一些不會被拒絕的禮,應當送些什麼好?”
張堯是跟著先齊王的舊人,算是看著蕭持長大的,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個人這麼上心過,是好事,張堯心里高興,痛快地應了一聲。
蕭持卻又覺得有些不妥。
“別說是朕要問的,算了,還是私下里打聽吧。”
張堯抬頭:“陛下是怕長公主殿下拿這事兒當話頭調侃您?”
蕭持轉坐到紫檀寶座上,心不在焉地說一句:“知道了定要見,鬧得不安生,再把教壞了……”
說完之后皺著眉頭看了看門口的方向,自己都沒察覺自己比以往話多,竟然還發起了牢:“怎麼換服這麼慢?”
張堯聽陛下談及榮昌公主,倒是很贊同地暗暗點頭,那可是大魏奇子,為人張揚古怪,在文那邊口碑可不怎麼好,畢竟后院里——
Advertisement
他正在那想事想出了神,忽然發現眼前一暗,蕭持從寶座上站起來,正看著他后面。
姜肆沒穿過這樣繁復的裳,盡管這已經是挑選的花樣最為簡單干凈的一套了,穿上去后發現自己連路都不會走了,好像步子邁著大一點都是給這裳抹黑。
拘謹扭著走進來,頭也不好意思抬,某一瞬間,想說還是換回去那干凈利落的短打吧,就算要做什麼擺也可以隨意扎到腰上,可這畢竟不是的家。
陛下嫌那服臟了,又能說什麼呢?
無奈地嘆了一聲,已走到近前,小心翼翼地拈著一看就價值不菲的織錦裾,輕輕跪下,輕輕叩首。
張堯滿意地打量著眼前的人,換了一服整個人的氣質也不一樣了,照他看,京城里也挑不出誰家的小姐比更惹眼,果然陛下的眼就是不一樣。
張堯等了等,沒聽見回應,他回頭一看,發現他家陛下竟然看出了神,雖然還是那副誰都看不的神,但如這般毫無反應就已經是反常了。
他抵著咳嗽一聲。
良久——
“平。”
姜肆下意識護著頭上的步搖輕輕直起子,又輕輕抬起站起來,蕭持看著僵的作,終是沒忍住輕笑出聲。
Advertisement
“連怎麼平都不會了?”
姜肆聽出他話中調侃,臉上一熱:“民實在是不習慣這些。”
“覺得不自在?還是不喜歡?”
陛下似乎很喜歡刨問底。
姜肆搖了搖頭,又害怕步搖甩到臉上,只敢輕輕晃下腦袋,無奈道:“都不是,是覺得不方便。”
蕭持走到前,姜肆覺鼻尖的沉香味道重了些,下意識想后退,便聽頭頂傳來他的聲音。
“你既已回到將軍府,有些禮儀規矩日后是一定要學的,穿打扮也一樣,不可以只隨自己喜好而來。”
姜肆茫然抬頭,不知他為何要跟說這些,而且也不聽。
“不過。”蕭持話鋒一轉。
“有個份,也可任你隨心所,放肆而為。”
姜肆不由得心跳加快,下意識問:“是什麼?”
追問的神太急切,迎上來的霧靄雙眸讓人生出一種難言的保護,蕭持雙手背在后,僵直的背脊忽然向前一。
姜肆覺他的臉在眼前放大,也不過是一個呼吸之間的事,剛剛還活蹦跳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嚇得后撤一步,手臂卻被人攥住。
蕭持眉頭輕皺,另一只手到頭頂,兩那支金步搖拔.出來,換了一個方向上:“應該是這樣。”
替戴好金步搖之后,蕭持推后一步,轉回到寶座前,卻沒再回頭,對道:“今日先如此,你回去吧。”
Advertisement
姜肆還沒從剛才的震驚中回過神來,惶惶地瞪大了雙眼,連呼吸都忘了,聽到陛下讓出去,下意識問:“不按了嗎?”
問完趕低下頭,胡行了一禮:“民告退!”
轉過匆匆離開,也不再邁什麼小碎步了,也不管頭頂上叮叮當當的頭飾了,大步流星地往殿外走。
張堯看著姜醫離開,回頭去看陛下,就見他正若有所思地看著自己的手。
看夠了,蕭持放下手,轉坐下,輕輕出了一口氣,張堯忍不住笑,哪知蕭持突然扭頭看他。
“朕方才,是不是嚇到了?”
張堯想寬陛下幾句,可惜良心他說實話。
“姜醫還是霍將軍名義上的正頭娘子,陛下這樣做,是會多心的。”
卻聽陛下冷笑一聲。
“尋常人家的兒早已經知道朕是何居心了,偏還一副懵懂無知的樣子。”
那語氣,也不知是不滿姜醫“鐵石心腸”而發的牢,還是因為心意得不到回應而自惱。
但不管如何,總歸是讓陛下多了點人味,這未嘗不是件好事。
張堯正喜滋滋地樂著,外面忽然有人通傳千統領求見,蕭持收起神,讓他進來,不消片刻,千流匆匆行進,單膝跪下:“陛下,二司傳來消息,齊王殿下三日后進京。”
Advertisement
蕭持的臉瞬間沉了下去。
姜肆坐上了馬車仍在想著養心殿發生的事,如果說之前賞賜那些金銀珠寶只是為了答謝的救命之恩,那方才陛下為戴金釵的舉絕對不正常,本不像他會做出來的事,可到底是為什麼呢?
姜肆想破了頭也不知陛下用意。
馬車很快回了將軍府,姜肆心里一團麻,下了馬車后悶頭向前走,不知不覺到了正廳門前。
抬頭一看是會松堂,霍岐可能在里面,心里就更煩悶,轉要走時,卻忽然聽到里面傳來一聲驚呼。
“你娘子還活著?”
猜你喜歡
-
完結1098 章

帝凰女毒天下
前世助夫登基,卻被堂姐、夫君利用殆盡,剜心而死。 含恨重生,回到大婚之前。 出嫁中途被新郎拒婚、羞辱——不卑不亢! 大婚當日被前夫渣男登門求娶——熱嘲冷諷:走錯門! 保家人、鬥渣叔、坑前夫、虐堂姐! 今生夫婿換人做,誓將堂姐渣夫踐踩入泥。 購神駒,添頭美女是個比女人還美的男人。 說好了是人情投資,怎麼把自己當本錢,投入他榻上? *一支帝凰簽,一句高僧預言“帝凰現天下安”, 風雲起,亂世至。 他摟著她,吸著她指尖的血為己解毒治病,一臉得瑟: “阿蘅,他們尋錯帝凰女了?” “他們不找錯,怎會偏宜你?” 他抱得更緊,使出美男三十六計……
176.4萬字8.38 401415 -
完結490 章

嫡女為謀
作為現代特種兵的隊長,一次執行任務的意外,她一朝穿越成了被心愛之人設計的沐家嫡女沐纖離。初來乍到,居然是出現在被皇后率領眾人捉奸在床的現場。她還是當事人之一?!她豈能乖乖坐以待斃?大殿之上,她為證清白,無懼于太子的身份威嚴,與之雄辯,只為了揪出罪魁禍首果斷殺伐。“說我與人私會穢亂宮闈,不好意思,太子殿下你親眼瞧見了嗎?””“說我與你私定終身情書傳情?不好意思,本小姐不識字兒。”“說我心狠手辣不知羞恥,不好意思,本小姐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斬草除根。從此她名噪一時,在府里,沒事還和姨娘庶妹斗一斗心機,日子倒也快活。卻不料,她這一切,都被腹黑的某人看在眼里,記在了心里……
108.5萬字8 94612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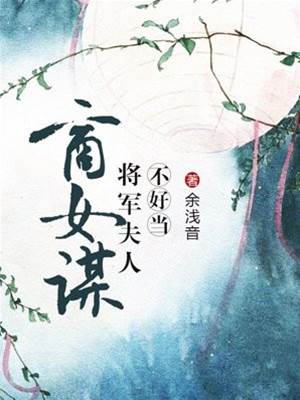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連載287 章

世子嫌棄,嫡女重生後轉嫁攝政王
雲念一直以為自己是爹娘最寵愛的人,直到表妹住進了家裏,她看著爹爹對她稱讚有加,看著母親為她換了雲念最愛的海棠花,看著竹馬對她噓寒問暖,暗衛對她死心塌地,看著哥哥為了她鞭打自己,看著未婚夫對她述說愛意,她哭鬧著去爭去搶,換來的是責罵禁閉,還有被淩遲的絕望痛苦。 重來一世,她再也不要爭搶了,爹爹娘親,竹馬暗衛,未婚夫和哥哥,她統統不要了,表妹想要就拿去,她隻想好好活下去,再找到上一輩子給自己收屍的恩人,然後報答他, 隻是恩人為何用那樣炙熱的眼神看她,為何哄著她看河燈看煙火,還說喜歡她。為何前世傷害她的人們又悲傷地看著她,懇求她別離開,說後悔了求原諒,她才不要原諒,今生她隻要一個人。 衛青玨是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從未有人敢正眼看他,可為何這個小女子看他的眼神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喜歡他? 罷了,這嬌柔又難養的女子也隻有他能消受了,不如收到自己身邊,成全她的心願,可當他問雲念擇婿標準時,她竟然說自己的暗衛就很不錯, 衛青玨把雲念堵在牆角,眼底是深沉熾熱的占有欲,他看她兔子一樣微紅的眼睛,咬牙威脅:“你敢嫁別人試試,我看誰不知死活敢娶我的王後。”
52.8萬字8.18 5789 -
完結301 章

第三十年明月夜
第三十年,明月夜,山河錦繡,月滿蓮池。 永安公主李楹,溫柔善良,卻在十六歲時離奇溺斃於宮中荷花池,帝痛不欲生,細察之下,發現公主是被駙馬推下池溺死,帝大怒,盡誅駙馬九族,駙馬出身門閥世家,經此一事,世家元氣大傷,寒門開始出將入相,太昌新政由此展開。 帝崩之後,史書因太昌新政稱其爲中興聖主,李楹之母姜妃,也因李楹之故,從宮女,登上貴妃、皇后的位置,最終登基稱帝,與太昌帝並稱二聖,而二聖所得到的一切,都源於早夭的愛女李楹。 三十年後,太平盛世,繁花似錦,天下人一邊惋惜着早夭的公主,一邊慶幸着公主的早夭,但魂魄徘徊在人間的小公主,卻穿着被溺斃時的綠羅裙,面容是停留在十六歲時的嬌柔秀美,她找到了心狠手辣、聲名狼藉但百病纏身的察事廳少卿崔珣,道:“我想請你,幫我查一個案子。” 她說:“我想請你查一查,是誰S了我?” 人惡於鬼,既已成魔,何必成佛? - 察事廳少卿崔珣,是以色事人的佞幸,是羅織冤獄的酷吏,是貪生怕死的降將,所做之惡,罄竹難書,天下人恨不得啖其肉食其血,按照慣例,失勢之後,便會被綁縛刑場,被百姓分其血肉,屍骨無存。 但他於牢獄之間,遍體鱗傷之時,卻見到了初見時的綠羅裙。 他被刑求至昏昏沉沉,聲音嘶啞問她:“爲何不走?” 她只道:“有事未了。” “何事未了?” “爲君,改命。”
48.8萬字8 60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