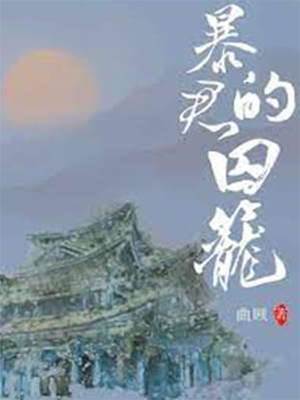《甜寵文里的反派女配》 第53章 第 53 章
沈嫿泡過澡后,從頭到腳紅了出來,趴在貴妃榻上任由杏仁拿著清涼膏為拭脖頸上的紅痕。
也不敢反駁說那不是蟲子咬的,只能老老實實地被塗得渾都是草藥味,蒙著臉等頭髮自然吹乾。
順便聽院中的丫頭像講故事般,說著近來府上發生的事。
趙溫窈的那個婢如月,病已經好全了,又回去繼續伺候,至於之前那個婢小寒,從圍場回來后莫名生了病。
懷著孕,怕被過了病氣,不敢再讓小寒伺候,就給賞了銀錢將人送出府去了。
核桃在一旁剝著蓮子,這是方才沈長洲讓人送過來的,夏日炎炎不適合吃煎炸之,便拿些這等消暑的小食給當零。
聽到們說起小寒,趕忙湊過來道:「表姑娘也真狠得下心,小寒對可忠心了,在圍場事發前,您不是讓奴婢看著們主僕嘛,小寒的手都燙得不樣子了。」
沈嫿是故意讓核桃盯著們兩的,為的就是讓趙溫窈覺得在阻止去見太子,這才能讓有危機,不得不想辦法去見太子。
果然趙溫窈也如所料,讓小寒借著去拿膏藥的機會找到了沈長儒,再由沈長儒帶著出了帳子。
甚至當時在陪著凌維舟,也是想辦法差人將引開的。
沈嫿自然不能辜負的一番苦心,很配合的計劃,只是多給加了一味佐料。
看來這個小寒知道不趙溫窈私的事,不然也不會這麼著急就將趕出府去,「可知道小寒如今的下落?」
「奴婢讓人盯著呢,您可要見見?」
「不急,先看著莫要讓出事,等尋著了人,再一塊見。」
核桃似懂非懂地點了點頭,像是想到了什麼,湊到耳畔低聲音道:「您讓人看著那個如月,方才有人來說,近來如月的行跡有些奇怪,時常往前院跑,與前頭有個管事瞧著很是曖昧。」
Advertisement
說到這個便神了,瞬間從榻上坐起,將屋的丫鬟們都屏退,神很是嚴肅地道:「仔細說說,是哪個管事?」
即便之前如月被打了板子,連床都下不了,也還是不敢掉以輕心,一直差人看著,先前都是相安無事,這趙溫窈一回府,便開始有小作了。
「是前院管門房的廖管事,長得有些野,一直沒娶媳婦。」
沈嫿知道那個管事,他跟了父親很多年,在府也很很能說得上話。曾在回府的路上試探過父親,是否會做出對不起母親的事來。
他當是經歷了凌維舟的事心中難過,沉了下道:「呦呦,為父知道你如今對天下男子皆是失戒備,但為父有一萬個納妾的機會,不管是同僚贈或是你祖母為了子嗣,你母親也並非不容人之人,也主說過為我納妾,能不能與做不做是兩回事。」
「你母親也是自小盡疼寵與護長大,為我吃盡苦頭生兒育,只有我一個丈夫,我又如何能再有旁人呢,就像我家呦呦是最好的,將來擇的夫婿,也得對我們呦呦一心一意才好。」
沈嫿不懷疑父親對母親的,但也架不住旁人的私詭計,尤其是有夢境帶來的預言,不得不防備著如月。
「這廖管事雖然野了些,但好歹跟了父親那麼多年,怎麼會到如今還未親,我記得他都快到而立之年了吧。」
「姑娘記好,聽說是廖管事年時有樁娃娃親,可惜方子弱,沒能挨到親的年歲就病逝了,廖管事便一直未娶。」
沈嫿越聽越皺眉,這個經歷怎麼還有幾分耳,遲疑了下,才反應過來,凌越不就是年時定下了蘇家的姑娘,但他那會在戰場殺敵。蘇姑娘福薄沒能等到他凱旋便病逝了,而他也是多年未娶,甚至沒聽說他有要說親的意思。
Advertisement
從未聽凌越提起過有關這位未婚妻的事,之前是沒想起來,如今想到了,便有些泛酸,他是為了才這麼多年未娶嗎。
能配得上他的,定是個聰慧貌的姑娘吧。
沈嫿一時想得出神,就聽核桃猜測著道:「這如月長得還算清秀,的年歲也不小了,早有不管事打聽過,您說是不是打得這個主意。」
回過神來,勾了勾角冷笑了聲,「人家的志向可遠不在此。」
一個小小的管事,又怎麼可能滿足得了這對主僕的胃口,沈嫿眼底閃過些許厭煩,真是粘上就甩也甩不掉的狗皮膏藥。
好在那日以凌維舟/為由,叮囑了父親,不許胡飲酒。
沈延雖然覺得有些奇怪,但他向來是妻子說了聽妻子的,兒說了聽兒的,想著剛了打擊,也沒多想就應下了。
沈嫿還與他擊了掌,父親一貫言出必行,相信他定能守約,如今唯一要防備的就是如月這邊了。
「讓人繼續盯著,再去前院找廖管事也告訴我。」
核桃認真記下,見熱得額頭滿是細汗,讓人再端了些冰來,打著扇子給納涼。
「對了,阿英的東西都收拾好了嗎?」
按照夢中的記憶,霍英的父親得歲末才會平反,但此番去白馬寺竟有意外的收穫,有日與凌越閑聊時說起了霍將軍的事。
不想凌越與霍將軍曾因增援打過道,他聽聞此事,很是看重,當下便差人去調查,幫著霍將軍的舊部搜集證據。
前些日子,那舊部已將證據呈上,也要跟隨一塊去奔走,不方便再住在沈家。
「都收拾的差不多了,您給租下的院子已布置好了,僕婦下人也都打點過了,王爺還派了個侍衛過去看守,絕不會出差池的。」
Advertisement
沈嫿這才放心下來:「讓人照看著,有什麼需要的及時與我說。」
後牽扯著沈家,且最近有些引人注目,過去送太過招搖,還是等穩定下來,案昭雪后再去恭賀的好。
很快屋重新安靜了下來,沈嫿看著手腕上細細的手鏈,忍不住泛起了相思。
那是條赤金盤螭的鏤空細手鏈,今早醒來時,就發現戴在了手腕上,手鏈很細只比的手腕要寬一些,自然地垂下時會出懸掛在上面的小掛飾。
是只純金打的小鹿,晃時像是小鹿在奔跑,靈又可,第一眼瞧見就喜歡極了。
知道是凌越給戴上的,可惜早上兄長在旁,都沒機會謝過他的禮。
這才分開半日,便開始想他了,往後見不著他的日子可該怎麼熬才好。
-
凌越回京后,沒有回王府而是直接去了大長公主府,夏后,大長公主的氣看著略好了些,也有神起來走了。
他到時,徐駙馬正在陪著對弈,旁邊有個小正在煎茶。
大長公主生平最喝茶,再嫁后,徐駙馬差人將大長公主府重新修葺過,
後院的屋舍都推翻了,空出的地全種上了茶樹,中央是個喝茶品茗的亭子,一條小渠圍繞著亭子,看上去儼然是個茶園。
有漫著清水的小渠環繞著,又有高大的綠植遮擋著,讓它仿若湖心小亭一般,不烈影響,清涼又悠閑。
大長公主雖然上了年紀,但雙目依舊明有神,遠遠就瞧見了他,笑瞇瞇地朝他招了招手。
「阿越來了,快些陪我下棋,與你姑父下棋真是沒意思了。」
並不是徐駙馬的棋藝不好,相反,他是京中出了名的聖手,棋風穩健縝,唯有凌越這般棋路奇詭偶爾能打他的陣腳。
Advertisement
偏偏他與大長公主下棋就讓著,不管被說了多回,總也忍不住地讓著。
唯有與凌越下棋,就算是輸了也能酣暢盡心。
凌越習慣了他們夫妻的相模式,自然地走過去坐下,徐駙馬被嫌棄也不覺得有什麼,反而還樂呵呵地起將小到一旁,「那我給你們沏茶。」
「和談書不是已經簽了,你近來也沒什麼事要忙吧,怎麼這麼早就過來了,不用陪著小姑娘了?」
大長公主邊落子,邊與他閑聊,這世上也就只有老人家,敢當著他的面調笑這煞神。
凌越面不改地封住的後路,毫不遮掩地直白道:「回府了。」
「難怪,我就說今兒怎麼臭著張臉,原來是小人分別了。」
凌越依舊行雲流水地落子:「不算分別。」
他向來做事坦,事無不可對人言,更何況這位姑母自小待他如親生子,他對沈嫿如此特殊,自然也瞞不住。
「小姑娘長得好脾氣也好,我老太婆喜歡得,真是便宜你這小子了,若是我有兒子,定要與你爭上一番才好。」
「您現在努努力,也未嘗不可。」
大長公主頓了下,被他氣得連棋子都丟了:「阿熹你快聽聽,這臭小子都說得是什麼話,居然連我都敢編排,我都多大年紀了,哪還生得齣兒子來。你這張毒,也不知道那丫頭是如何得了你的。」
可不只有說話一個用,凌越想著小姑娘環著他脖頸時,又乖巧的勁,目不覺黯了黯。
徐駙馬端著剛沏好的茶與梅子過來,樂呵呵地哄了好幾句,才算把給哄住。
大長公主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轉頭又與他繼續說道:「我說真的,你若誠心與在一塊,這麼沒名沒分的也不行,還是早些把人定下來才安心。前兒我還聽說,貴妃要為太子挑選新婦,太子怎麼都不肯,說是只願娶沈家那丫頭。」
「你可別以為退了親就萬事大吉了,一家好百家求。你脾氣又差又毒,還比人家年長這麼多歲,不趕將人定下來,小心跑了。」
從凌維舟找去白馬寺,凌越就知道他賊心不死,聞言出個譏諷笑來,「他也配。」
「不管怎麼說他總是太子,份擺在這,若再來個什麼聖旨賜婚,你看配不配。」
他的目一凜,薄輕啟極盡冷漠地道:「那便讓他滾下去。」
大長公主微微一愣,只不過是懶得管外頭的事,但不代表真的眼瞎耳聾,相反宮發生的事皆是一清一楚。
之前就聽到了些許風聲,說凌越與三皇子走得近,還當是賢妃等人故意攀扯,沒想到竟是真的。
出了些許詫異之:「你不是最不喜爭權奪嫡之事……」
「只要不是他當太子,誰當都一樣。」
他說得輕描淡寫,好似換太子在他眼裡,就像是換個侍從一樣簡單。
大長公主也不喜凌維舟,本就覺得他弱無能,最近的事出了之後,更是覺得此人難當大任。
但更換儲君,對社稷的穩定影響還是很大的,猶豫了下道:「但太子素有賢名,之前陛下臥床不起,他代理朝政也還過得去,憑一個名聲問題,恐怕還不足以廢除他。」
太子是祭天啟聖昭告天下正式冊封的,即便太子最近確是犯了幾件錯事,可子而已,朝臣和百姓都不會當一回。
他既無不敬長輩也未結黨營私,更無十惡不赦的大罪,帝便是真的心中不喜他,也沒理由廢他。
凌越當然明白的意思,卻仍是面不改,他抿了口杯中的白茶,往桌上一擺冷聲道:「沒理由,便讓他有。」
饒是大長公主這般守過城池,滿手沾過鮮的中英豪,也被他渾上下那戾氣所震懾。
險些要口而出,既是旁人都能坐得那個位置,你為何不自己去坐那個位置。
同樣是龍子孫,疆域穩定靠得是他,大雍百姓的安危靠得也是他,可換來的是上位者的猜忌與戒防,甚至想著法的削弱他的兵權。
與其日日防著那對窩囊廢父子,扶個別人上位,為何不能取而代之。
但大長公主同樣也了解這個侄兒,讓他領兵打仗可以,讓他治理國家卻有些為難。並非能力,而是他本就不屑於那張龍椅。
要說,帝才是真的蠢,若凌越真想謀逆,當初三王了舉兵謀反時,他便可借著捉拿逆賊的機會,揮兵京城劍指宮牆,皇位與他而言唾手可得,他只不過是不稀罕罷了。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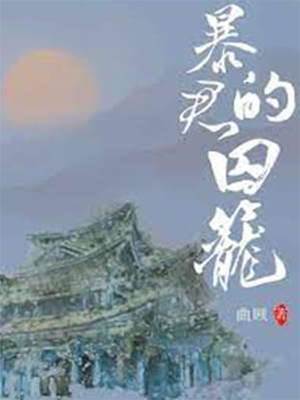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2913 章
妃本良善:皇上請下堂
他是西玄冷漠狠戾的王,卻因一名女子,一夜癲狂,華發如霜。她,便是大臣口中被他專寵的佞侍。“除了朕,誰都不能碰她!” 案一宮宴,某女給了挑釁妃子一記耳光“勾心鬥角太累,本宮喜歡簡單粗暴。” 某帝“手疼不疼?” 某女斜睨某妃“這就是我跟你的差別,懂?” 案二某帝鳳眸輕抬“把朕推給其他嬪妃,朕在你心裏就那麼不值錢?” 某女聳肩“不就是個男人?我若想要,滿大街的男人任我挑。” 轉身某女便被吃幹抹淨,某帝饜足哼笑,“挑?”
262萬字8.18 49515 -
完結300 章
和親太子妃的千層馬甲
北燕太子迎娶盛涼公主前夕,小乞丐阿照被送上和親馬車,成了嫁妝最多的代嫁公主。面對太子的厭惡找茬,阿照不悲不喜,從容面對。然而,當昔日故人一個個對面相見不相識時,陰謀、詭計、陷害接踵而來,阿照是否還能從容應對?當隱藏的身份被一層層揭開,那些被隱藏的真相是否漸漸浮出了水面? ――##1V1##―― 她是喜歡周游列國游山玩水的天真少女,也是循規蹈矩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 她是和親異國的代嫁太子妃,也是那陰狠公子豢養在身邊的丑奴。 她是街角蓬頭垢面討飯的小乞丐,也是他國攝政王贈予金令的干閨女…… ―...
54.2萬字8 7262 -
完結154 章

冷美人撩完就跑,瘋批王爺哭著找
【清冷釣係舞姬(有隱藏身份)X不近女色瘋批王爺】【類似追妻 強製愛 男外強內戀愛腦 複仇 雙潔HE】不近女色的王爺蕭以墨,竟從別人手中奪了清冷金絲雀可江念綺與其他貴子的美人不一樣,不爭不搶不求名分蕭以墨擒住她下巴:“念綺,你難道不想當王妃?”“我自是有自知之明,不會奢求那些。”江念綺清冷的眉眼淺然一笑,這一笑卻讓他愈發瘋狂世人說她是個聰明人,乖乖跟著王爺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她肯定離不開王爺,就連蕭以墨自己也這麼認為但當蕭以墨替她奪了這天下,想要納她入宮時江念綺卻連夜逃走了,悄無聲息。“她肯定以為朕要娶世族貴女為後,跟朕鬧脾氣了。”正在高興她吃醋時,探子來報,她當初竟是有預謀接近,故意利用他的權勢複仇。蕭以墨胸口瞬間疼的心慌意亂:“朕寵著她,哄著她,可她竟在朕眼皮底下跑了。”再見時,那孤傲又不可一世的蕭以墨把她摁在懷裏。嘶啞低哄:“念綺,跟朕回去,好不好?”【偏女主控,瘋批霸道強製愛,類似追妻火葬場,重甜輕虐】
28.2萬字8 19107 -
完結124 章

吾妻甚是迷人
【嬌軟妖精X清冷太子,雙潔/重生/超甜!超撩!兄長超強助攻!】天凰國嫡出四公主溫若初,傳聞容貌驚人,如仙如魅,琴棋書畫無一不精通。是世間難得的嬌軟美人。眾人不知的是,自小兄長便在她房中掛起一副畫像,告訴她畫中之人是她夫君。一朝被害失去大部分記憶,她終於見到了畫中的夫君,比畫中來得更為清俊矜貴,身為顏控的她自然眼巴巴地跟了上去。“夫君,抱我~”“......”元啟國太子殿下,生性涼薄,宛如高懸明月。自及冠那年,一直困擾在一段夢鏡中,夢中之人在他求娶之時,轉嫁他人。尋人三年,了無音訊。正當放棄之時,在一處淺灘上遇到那女子,她嬌軟地撲向他,叫他夫君。劇場一花采節在即,京城各家貴女鉚足了勁兒爭奪太子妃之位。豈料霽月清風的太子殿下,親自從民間帶回了一名女子養在府中,各方多加打探均未知曉此女子的身份。眾人皆笑太子殿下竟為美色自甘墮落,高嶺之花跌落神壇;未曾想太子大婚當日,天凰國新任國君奉上萬裏紅裝,數不盡的金銀珠寶從天凰運送至元啟,並簽下了兩國百年通商免稅條約,驚得等看笑話的眾人閉了嘴,這哪是路邊的野薔薇,明明是四國中最尊貴的那朵嬌花!
22.9萬字8 14339 -
完結121 章

在遠古養大蛇
宋許意外成爲了一名遠古叢林裏的部落獸人,獸型是松鼠。 她所在的小部落被猛獸部落攻佔合併,宋許獨自逃進一片黑暗森林。 這片森林被一個蛇類半獸人所佔據,作爲一個曾經的爬寵愛好者,宋許看着漂亮蛇蛇狂喜。 宋許:好漂亮的尾巴!我完全可以!Boki!
20萬字8 14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