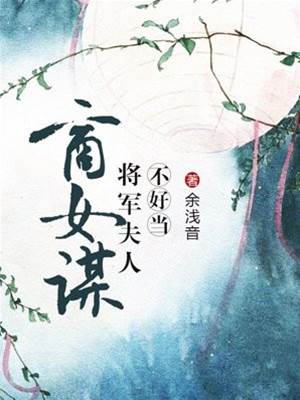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元配》 第7章 不一樣
年前,魏家請過掌櫃,又給掌櫃夥計的都發了過年的銀錢,鋪子便正式放年假了。魏家這裏還有些年禮有走,譬如,幾家生意往來人家,還有就是魏家的親家趙家。
這些,就是魏家男人們的事了。
不過,有一樁,是魏銀做的,那就是,給房東許家送了兩包點心兩條魚,還有就是明年的房租。
要,魏家也不是沒錢在北京城置宅子,可就像魏老太太的,咱們有家啊,咱們家不在北京城,在北京,這是來做生意的,以後老了,還是要回老家的。
所以,完全沒必要在北京城置宅子。
於是,魏家這些年,一直是租別人宅子住。
好在,這院子也不,三進院子,二十幾間屋子,足夠魏家人住了。
給許家送房租的事,魏銀著陳萱一道去。魏銀的話,“讓二嫂去認認門兒。”
“有什麽好認的,就是前後院。”魏老太太嘟囔著,掀開大鍋,一陣燉的濃香便撲麵而來,不要廚房,就是整個魏家,都給這燉香的了不得。李氏遞上筷子,魏老太太接了筷子在上一紮,便紮了個通,魏老太太笑的眉眼彎一線,“這好了,別再添柴了。”
李氏應一聲。
魏老太太回頭見陳萱在一畔站著還往鍋裏瞅,遂揮了揮手,“去吧去吧,你親那,許太太也是來過的,去認認門也好,前後鄰的住著。”
陳萱知道向來年下燉,魏老太太要吃第一口,如今這燉好,魏老太太想是擔心留下來吃燉,方打發同魏銀一道出去。陳萱也不多,雖也喜歡吃燉,可還沒到饞的地步,就同魏銀去了。
Advertisement
陳萱回屋把出門的大換上了,魏銀也換了新大,倆人相視一笑,魏銀拎著點心包,陳萱提著竹籃,裏頭是兩條凍魚。許家這原是四進宅院,是祖上傳下來的,如今許家老爺也沒什麽營生,就指著賃院子的銀錢過日子。許太太見著魏銀陳萱過來,連忙自廚下出來,熱的招呼倆人進屋。
許家也是舊式人家,不過,同魏家做生意的人家不同,許家祖上是念書的。一進他家堂屋,迎麵而來的就是正堂牆上掛的一幅花卉卷軸,卷軸兩側是相夷對聯,至於寫了什麽,陳萱就不認得了。許太太在上首坐了,請魏家這對姑嫂也坐,許家的那位姨太太已是洗手端了熱滾滾的茶來,許太太笑看向陳萱,“今年府上添了人口,我一直想過去同你家老太太話吶,偏生不是這事兒就是那事兒,倒是你們先過來了。”同陳萱魏銀問了好。
二容上禮,許太太直客氣。
魏銀又送上明年的租金,許太太笑接了,同那位姨太太道,“咱們新蒸的高梁紅棗的粘窩窩,這會兒正是好吃,拿兩個給阿銀和二嚐嚐。”
陳萱見許太太穿的是一洗的發白的棉旗袍,上的首飾不過耳朵上一對細細的銀耳圈,倒與自己戴的有些相似。魏家賃的是許家三進宅院,許家自己住的,反就是這一截開的大院子,院子雖大,也不過十來間房,可見許家生活並不寬裕。而且,據陳萱上輩子知道的,許家六個孩子,不論兒都要去學堂念書,每年又是一筆不開銷。許家不是富裕人家,就是他家的粘窩窩,怕也隻有在過年時才會蒸上一些,陳萱覺著不大好意思留下吃,魏銀同許太太很,已是笑瞇瞇的應承了,“唉喲,我年年冬就盼著許嬸嬸你蒸的粘窩窩。”
Advertisement
許太太笑,“阿銀你是常來的,二是頭一遭,二莫拘束,我家老爺同府上老太爺是極好,隻當自家就是。”
陳萱連忙應了。
許姨太太端著個黑漆茶盤進來,茶盤上兩個瓷碗兩雙木筷,一碗裏放了一個新出鍋熱氣騰騰的高梁米和了紅棗蒸的窩頭,因高梁米發黏,故而粘窩窩。別看北京城裏許多高檔飯食陳萱不一定見過,但這粘窩窩,以前在老家過年時,嬸嬸也要蒸的。見魏銀接過碗吃了,陳萱也沒推卻,接過嚐了嚐,的確好吃,高梁麵好,棗也甜。陳萱道,“這窩窩蒸得好吃。”
許太太笑,“這是我們院裏的老棗樹結的棗,這樹也有兩三百年了,每年八月十五打了棗,我都曬了存起來,年下使著蒸粘窩窩吃。高梁麵是我們鄉下的一位族叔給的,我嚐著,以往年在麵鋪子裏買的要好些。”
對米麵,陳萱再悉不過,,“這是今年的新麵。”
許太太越發高興,“是。”
魏銀問,“許嬸嬸,二妹三妹不在家麽?”這問的是許太太家的兩個閨。
許太太道,“們今學校放假,估計是學裏的先生有課業待,一會兒就回來了。”
因著許家兩位姑娘不在,而且,過年家家都忙,所以,吃過許家的粘窩窩,魏銀陳萱就告辭回家了。許太太很客氣的讓家裏姨太太裝了一大青花碗的粘窩窩,請魏銀帶回去給魏家老太太、老太爺嚐嚐。
魏銀也沒客氣,謝過許太太,就與陳萱回家去了。
倆人回家時,魏老太太果然已經吃過燉了。這倒不是陳萱神機妙算,是年下這燉的鹹,魏老太太一上午就喝了三茶缸子水,卻茅房數次。
Advertisement
上午燉,下午炸魚。
除了要過油的大鯉魚,還有就是一瓦盆的銀魚,這種魚極,不過寸許大,收拾好了裹上麵糊炸個,是極下飯的。魏家人都吃這口,魏銀也跟著一起在廚下忙,時不時的就要拈一隻來吃。魏銀一向討人喜歡,不是隻自己吃,一時還要喂大嫂、二嫂吃,魏老太太瞧見,難免念叨一回,“年還沒過,就都你們吃沒了。”
“炸出來還不就是人吃的。”魏銀道,“媽,我給你在灶上熱了饅頭,就著這剛炸好的魚,你跟阿雲吃兩口吧。”
魏老太太頓時沒意見了。
後半晌的時候,許家兩位姑娘過來找魏銀玩兒。
魏銀拿零心,三人去魏銀屋裏話,待許家兩位姑娘走時,陳萱把洗好的大青花碗拿出來,笑道,“正好一道帶回去。”
魏銀一拍腦門兒,笑,“看我,都忘了,省得我再跑一趟了。”把碗給許家兩位姑娘帶了回去。
其實,陳萱有些事想不通的,私下同魏銀,“阿銀,你比我聰明,你幫我想想。實在的,我看,許家家境一般,你,怎麽許家這麽多孩子還要念書呢?我聽,念書貴的,北京城的學堂更貴,要是許家孩子不念書,出去尋些營生,日子肯定比現在好過。”
“許家跟咱家不一樣,他家是書香人家,祖上就是念書的。你看,家裏都窮那樣了,我同二嫂,咱家雖不算有錢的,可平日裏吃穿總不愁。許家一三頓,平日裏就是鹹菜大醬窩窩頭,可就這樣,許家叔叔連家裏孩子都要供著念書。”著,魏銀將手一攤,無奈道,“咱家就不,咱們家,就男人念書,人都不識字,人家現在都管這睜眼瞎。阿雲這麽大了,也不念呢。要我,這都是舊觀念。”
Advertisement
“許家,我看也是舊派人家,他家還有姨太太吶。”陳萱。
“人家娶媳婦上舊,念書上可不舊。”魏銀快人快語。
陳萱才知道,原來,世上的人家也不都是一樣的。
陳萱又,“阿銀你不識字麽,我看你識字的啊?”
“那都是二哥以前念書,我偶爾學的。念書有什麽難的啊,爹是不我念,要是我念,我一準兒能考上那個大學的學堂。”魏銀很是同二嫂嘀咕了一回。
猜你喜歡
-
完結1098 章

帝凰女毒天下
前世助夫登基,卻被堂姐、夫君利用殆盡,剜心而死。 含恨重生,回到大婚之前。 出嫁中途被新郎拒婚、羞辱——不卑不亢! 大婚當日被前夫渣男登門求娶——熱嘲冷諷:走錯門! 保家人、鬥渣叔、坑前夫、虐堂姐! 今生夫婿換人做,誓將堂姐渣夫踐踩入泥。 購神駒,添頭美女是個比女人還美的男人。 說好了是人情投資,怎麼把自己當本錢,投入他榻上? *一支帝凰簽,一句高僧預言“帝凰現天下安”, 風雲起,亂世至。 他摟著她,吸著她指尖的血為己解毒治病,一臉得瑟: “阿蘅,他們尋錯帝凰女了?” “他們不找錯,怎會偏宜你?” 他抱得更緊,使出美男三十六計……
176.4萬字8.38 401415 -
完結490 章

嫡女為謀
作為現代特種兵的隊長,一次執行任務的意外,她一朝穿越成了被心愛之人設計的沐家嫡女沐纖離。初來乍到,居然是出現在被皇后率領眾人捉奸在床的現場。她還是當事人之一?!她豈能乖乖坐以待斃?大殿之上,她為證清白,無懼于太子的身份威嚴,與之雄辯,只為了揪出罪魁禍首果斷殺伐。“說我與人私會穢亂宮闈,不好意思,太子殿下你親眼瞧見了嗎?””“說我與你私定終身情書傳情?不好意思,本小姐不識字兒。”“說我心狠手辣不知羞恥,不好意思,本小姐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斬草除根。從此她名噪一時,在府里,沒事還和姨娘庶妹斗一斗心機,日子倒也快活。卻不料,她這一切,都被腹黑的某人看在眼里,記在了心里……
108.5萬字8 94612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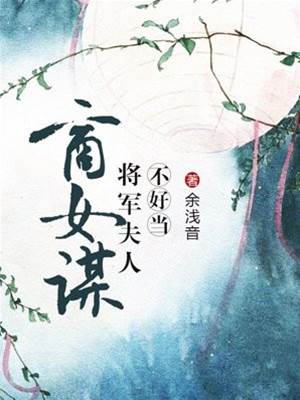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連載287 章

世子嫌棄,嫡女重生後轉嫁攝政王
雲念一直以為自己是爹娘最寵愛的人,直到表妹住進了家裏,她看著爹爹對她稱讚有加,看著母親為她換了雲念最愛的海棠花,看著竹馬對她噓寒問暖,暗衛對她死心塌地,看著哥哥為了她鞭打自己,看著未婚夫對她述說愛意,她哭鬧著去爭去搶,換來的是責罵禁閉,還有被淩遲的絕望痛苦。 重來一世,她再也不要爭搶了,爹爹娘親,竹馬暗衛,未婚夫和哥哥,她統統不要了,表妹想要就拿去,她隻想好好活下去,再找到上一輩子給自己收屍的恩人,然後報答他, 隻是恩人為何用那樣炙熱的眼神看她,為何哄著她看河燈看煙火,還說喜歡她。為何前世傷害她的人們又悲傷地看著她,懇求她別離開,說後悔了求原諒,她才不要原諒,今生她隻要一個人。 衛青玨是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從未有人敢正眼看他,可為何這個小女子看他的眼神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喜歡他? 罷了,這嬌柔又難養的女子也隻有他能消受了,不如收到自己身邊,成全她的心願,可當他問雲念擇婿標準時,她竟然說自己的暗衛就很不錯, 衛青玨把雲念堵在牆角,眼底是深沉熾熱的占有欲,他看她兔子一樣微紅的眼睛,咬牙威脅:“你敢嫁別人試試,我看誰不知死活敢娶我的王後。”
52.8萬字8.18 5789 -
完結301 章

第三十年明月夜
第三十年,明月夜,山河錦繡,月滿蓮池。 永安公主李楹,溫柔善良,卻在十六歲時離奇溺斃於宮中荷花池,帝痛不欲生,細察之下,發現公主是被駙馬推下池溺死,帝大怒,盡誅駙馬九族,駙馬出身門閥世家,經此一事,世家元氣大傷,寒門開始出將入相,太昌新政由此展開。 帝崩之後,史書因太昌新政稱其爲中興聖主,李楹之母姜妃,也因李楹之故,從宮女,登上貴妃、皇后的位置,最終登基稱帝,與太昌帝並稱二聖,而二聖所得到的一切,都源於早夭的愛女李楹。 三十年後,太平盛世,繁花似錦,天下人一邊惋惜着早夭的公主,一邊慶幸着公主的早夭,但魂魄徘徊在人間的小公主,卻穿着被溺斃時的綠羅裙,面容是停留在十六歲時的嬌柔秀美,她找到了心狠手辣、聲名狼藉但百病纏身的察事廳少卿崔珣,道:“我想請你,幫我查一個案子。” 她說:“我想請你查一查,是誰S了我?” 人惡於鬼,既已成魔,何必成佛? - 察事廳少卿崔珣,是以色事人的佞幸,是羅織冤獄的酷吏,是貪生怕死的降將,所做之惡,罄竹難書,天下人恨不得啖其肉食其血,按照慣例,失勢之後,便會被綁縛刑場,被百姓分其血肉,屍骨無存。 但他於牢獄之間,遍體鱗傷之時,卻見到了初見時的綠羅裙。 他被刑求至昏昏沉沉,聲音嘶啞問她:“爲何不走?” 她只道:“有事未了。” “何事未了?” “爲君,改命。”
48.8萬字8 60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