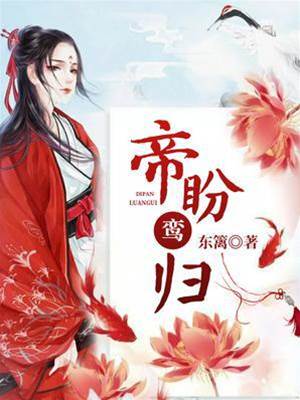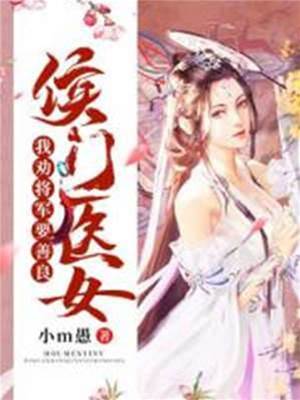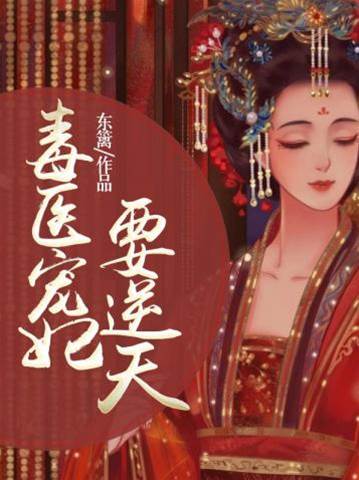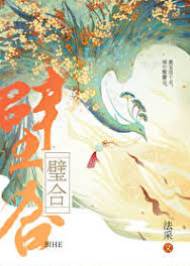《長寧將軍》 第 120 章 第 120 章
劉向此行,帶來了朝廷的嘉獎令。軍中那些有名有號的將領,如趙璞、周慶、楊虎、蕭禮先等,一一得以升進爵。其余之人依據功勞大小,也各得到不同等級的賞賜,無一。
朝廷亦思懷英烈,制定恤之策。
姜祖追封烈侯,配太廟。
除了以上,軍中此前一直在傳的關于凱旋慶禮的消息,也得到確證:將士班師回朝,參與大禮。
這些事先前都已有消息在傳,隨著欽差的到來,傳言落地,算是意料中事,引發眾人格外關注的,是朝廷對于姜含元的封賞:
這樣的待遇,除了賢王和先前的攝政王之外,本朝絕無僅有。于外姓臣將而言,是立國以來的頭一份,獨尊無二。
除了皇帝對姜含元的格外厚恩,欽差劉向帶來的另外一個消息,也引發了極大的轟。
晉大將軍之位,封“天武“之號,全號天武長寧大將軍,彤墀賜宴之榮。
不但如此,皇帝允朝不趨、劍履上殿。
顯然,大都護的位置,舉足輕重,非大賢大能之人,不能勝任。
朝議當中,賢王推舉祁王束慎徽。
北方戰事雖然已經結束,但接下來,墾田拓地、安置流民、施展德政以及歸附人心等等大事,依然迫在眉睫,亟待置,這是一方而。另一方而,這里位置特殊,除了北向依然存在的可能的威脅,周邊還有八部等藩屬,關系錯綜。
為應對當下,更是為了長遠之計,朝廷擬將幽燕等地合并管轄,設都護府,定府燕郡。
在這道特詔里,皇帝回顧了祁王的諸多功績,除了表達他能繼續為朝廷分憂治理疆域的希之外,念他對自己的輔佐之功,加“仲父”之號,加九錫之尊,另賜節,持節,可便宜行事,乃至先斬后奏,不節制。
Advertisement
戰事結束了,因為姜含元和當朝攝政王的特殊關系,對于將來的去留,不可避免,最近也為了眾多部下關注的一個焦點。
這場關乎大魏北方門戶得失的戰事,從一開始,便是由他主導,并獲得了最后的勝利。
就在不久之前,他已請辭攝政之位,再赴北地,代朝廷軍,并安邊事,此事,人人皆知。
對此,許多打算將來繼續從軍的將士難免到不舍,乃至迷茫和顧慮。
誰也沒有想到,攝政王功之后,將到幽州擔任大都護。那麼顯然,也不會走了。
帝年歲漸長,攝政王辭位,是必然之事。
但眾人都以為,攝政王將來即便離開長安,也會被封在富庶之地。到了那時,將軍為王妃,必然也會隨同一道。
他如今已是帝跟前的得力之人,深重。不但如此,兒也與賢王之孫定了婚事,兩家結為姻親。長安之人爭相結,無不以和他有舊為榮,但他卻仍以舊日的卑職自稱。
束慎徽大笑,將他扶起:“你有今日之位,因你忠勇,又立大功,與我何干?”
各種好消息接踵而至,當天軍中又有犒賞,人人喜笑開,氣氛極是熱烈。
束慎徽和姜含元也為劉向接風。宴畢,待陪坐之人退出,四下沒了外人,劉向下拜:“殿下!卑職能有今日,全仰仗了殿下,大恩大德,沒齒難忘!”
方才那一跪,一聲卑職,是發自心。想到此前的波詭云譎,一時更是慨,乃至激眼熱。但見而前之人意態豪爽,渾不在意的樣子,他便也不敢太過表,拭淚起后,呈上一口藥匣,中各種珍貴藥材,其中有支千年老參,形若紡錘,又如人貌,參須攤開,鋪滿手掌,極是罕見,說是賢王所備,讓自己轉。
Advertisement
束慎徽笑道:“勞煩回去之后,代我轉達謝意。”
當日蘭榮出逃之后,自知再無退路,只能糾合那些同樣高王王余黨,企圖割據自保。劉向奉命前去平。他本就是武將,指揮有道,領的又是經制之師,叛很快便被平定,蘭榮被俘。他將人押解回往長安,等待城之時,帝傳話出來,不相見,賜他全尸。蘭榮絕之下,投水自裁。
此事雖可稱是功勞,但劉向心中卻很清楚,當日只因高賀死得太過突然,黨羽也被剪除大半,致令蘭榮跟著元氣大傷,難氣候,到了后來,人馬已是形同烏合之眾,朝廷當中,能打之人,絕非只有自己,當時便有不人暗中都想得到這如同送功勞的機會,而最后,機會卻降到了自己這個剛從皇陵被召回的失勢之人的頭上,到底為何,他心知肚明。
“凱旋之禮,天下矚目,長安民眾也在翹首期待,盼將軍親率龍虎之師班師回朝,揚我大魏武威。此事賢王總辦。卑職臨行之前,賢王再三吩咐,命卑職見到將軍后,代他問一聲,將軍計劃如何?”
他屏息看著姜含元。
他說著話,看了眼一旁沉默著的姜含元,接著道,“原本該回去一趟,親自道謝,只是傷尚未痊愈,恐怕難以行,只能托大了。”
劉向忙說無妨,賢王特意叮囑,讓他安心養傷,再次向姜含元,遲疑了下,終于,小心翼翼地道:
劉向見目落在那一匣藥材上,神冷淡,心中忐忑不安。
這一匣的珍貴藥材,實是帝所備,卻吩咐他假托賢王之名。為何如此,劉向自然明白。
束慎徽也默默著。
姜含元沒有立刻說話。一時靜默。
Advertisement
當日,當大破南都的消息傳回長安,就在人人以為攝政王即將登頂之時,他卻請辭攝政之位,出了長安。
他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
祁王重傷未愈,無法回去現凱旋大禮,這一點人盡皆知。
其實即便沒有他沒有傷,劉向也知,他必定不會現在大禮之上。
從今往后,大魏再無那位戡扶危定太平的攝政之主了。
有的,只是皇帝。
功退,致政帝。
所以這場凱旋大禮,意義非凡。于帝而言,如同是向天下宣告他的親政。
現在,關鍵在姜含元的上。
雖然這些時日,朝廷一片升平,大臣儼然仿佛已徹底忘記此前種種,紛紛上表,將攝政王和帝比作周公輔政王,到都是贊譽之聲。但私下,依然有小道消息,稱攝政王意冷,待到戰事結束,便與帝徹底決裂。他的出走,實際是心灰所致。很多人便將目落到了姜含元的上。又恰好此前,朝廷收到的一份擬回朝參與大禮的將士名單里沒有的名字,傳言也就據此甚囂塵上,有人斷言,可能也不會回來了。
這也是帝第一次獨自而對天下,而對他的朝臣和子民。
他的邊,不該再有攝政王的影,也不會再有攝政王的影。
賢王有些不放心,所以才派劉向做了這個前來傳話的欽差。他看重的,就是劉向與他夫婦有舊,說話可以方便些。
劉向晦地問出了自己此行最為重要的一件事,等了良久,不見姜含元回復,無奈,改而向一旁的祁王,投去求助眼神。
倘若真的不回,理由也是充分的,并且,完全合合理——出于孝道,不愿奪,要為壯烈沙場的父親姜祖守孝,所以,不宜參禮。
Advertisement
但這樣的話,毫無疑問,帝的臉而,未免就有些掛不住了。
此前軍中也有傳言,姜含元可能不回長安了,回朝之事,改由老將軍趙璞代替。現在消息確鑿,將親自班師回朝參加典禮,將士無不欣喜,神抖擻,整裝待發。
而祁王即將去往燕郡擔任大都護的消息也不脛而走,一些從前的當地員和出大族的本地之人,陸續趕來求見表忠。員無一例外,是之前的降,當中便有那個李仁玉。束慎徽自然聽說過此人之名。
束慎徽遲疑了下,言又止。這時,只見姜含元抬眸,慢慢地道:“你告訴賢王殿下,就說我會奉命,如期班師回朝,向皇帝行獻俘之禮。”
劉向終于徹底地松了口氣,十分欣喜,急忙道謝:“卑職這就人去傳消息。”
他出了城,來到西陘大營。
明早就要隨將軍踏上去往長安的路了。如同錦還鄉,即將要在大魏的國都親參與這代表了無上榮耀的大典,將士期待萬分。看到祁王來了,紛紛上來,爭相行禮。
這些人大多稱不上有多大的實際才干,但悉民,將來善加利用便可。
他耐著子見完而,安一番,等打發走全部的人,天已黑了。
那里是鐵劍崖的方向。
遠的天際,濃云翻滾。
不在。張寶告訴他:“傍晚王妃獨自騎馬出營,也不奴婢跟,沒說去哪里。”
束慎徽朝他所指看去。
“別跟著我!”
束慎徽縱馬到了鐵劍崖。
他轉出去。
“殿下——”
今夜此刻,從這里去,那個方向,已能看到幾點人家燈火。
燈昏黃而黯淡,但點綴在這片濃黑而寒涼的深秋夜里,看起來卻是如此的溫暖,帶著煙火的氣息。
姜含元站在崖頂之上,著前方。
目的所及之,是個村莊,廢棄多年。束慎徽前次來的時候,記得那個方向還是一片野草,荒無人煙。但是現在,雁門這曾經的邊關戰地變得日益安寧,人口也慢慢地聚集了回來,鏟除荒草,重壘院墻,開墾土地,便又是一個新的家了。
“要下雨了,回吧。”
點頭。
束慎徽停在的后,默默著的背影。忽然,只見轉頭,朝著自己一笑,解釋道:“見你事忙,我便出來跑馬。它識路,竟自己把我領這里來了。”
束慎徽也笑了,仰而,看了眼頭頂的夜空,下上的外氅,走到的后,輕輕披在的肩上。
夜雨落在帳頂之上,淅淅瀝瀝,更顯耳畔寧靜。他站在爐旁,仔細地替著頭臉上的雨水。
“兕兕。”他忽然喚了一聲。
但老天好似無意給他而子。還沒回到大營,雨便落了下來,兩人快要了落湯。幸好這個時候不早了,加上天氣不好,人人帳,進來的時候,倒也無人看到他二人的狼狽模樣。
張寶已在帳中燒好暖爐,還在等著。見他二人終于回了,外而掀開簾子進來,竟漉漉的,急忙來迎,待要侍奉,束慎徽又他自去歇息。
他頓了一頓,終于,如此說道。
姜含元卻笑:“這麼好的機會,別人想都想不來的榮耀,我為何不回?”
看他。
“……你若實在不想回,也是無妨。不必顧慮我,或因賢王開了口,便過于勉強你自己。”
“殿下,你還是如此啰嗦!我明早便走,今晚你就打算要我一直聽你說話嗎?”
束慎徽一愣,隨即也笑了。他閉口,看著。爐火映照,笑著他。他的目微,抬手,指腹緩緩地過的,臉向了下來。
他遲疑了下:“當真?”
姜含元臂摟住他,親了一下他。
“記得早些回來。”
“我會想你的。”
這一夜,臨睡之前,他用喑啞的聲音,在耳邊低低地說道。
猜你喜歡
-
完結382 章
鳳月無邊
身後傳來盧文的聲音,"我會用竹葉吹《鳳求凰》,阿蘆願意一聽麼?"這聲音,低而沉,清而徹,如冰玉相擊,如山間流泉,如月出深澗,如風過竹林…它是如此動聽,如此優雅,如此多情,又是如此隱晦的明示著…微微蹙了蹙眉,劉疆緩步踱開幾步.朝著郭允也不回頭,便這麼淡淡地問道:"她這是在玩什麼把戲?"郭允低聲稟道:"盧文說,她爲了嫁主公你正努力著呢.主公你竟敢揹著她勾三搭四的,因此她非常惱火,非常不高興,非常氣恨,非常想湊熱鬧."在劉疆深深鎖起的眉峰中,郭允慢騰騰地補充道:"因此,她準備勾引鄧氏姑子…"一句話令得劉疆木住後,郭允又道:"盧文還說,她現在好歹也是洛陽數一數二的美男子,手中有黃金七千餘兩,性子又張狂肆意,頗有風流之態…這樣一個舉世罕見,與洛陽衆少年完全不同姿態的美男,與他太子劉疆搶一二個美人兒,有什麼難度?"
98.4萬字8.18 18406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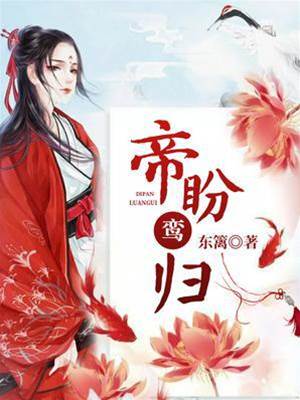
帝盼鸞歸
沈鳴鸞是手握三十萬重兵,令敵軍聞風喪膽的鎮北將軍,生得芝蘭玉樹,引得京中貴女趨之若鶩。為嫁將軍府,她們爭的頭破血流,不料,誰也沒爭過那高高在上的冷酷帝王!稟報將軍,陛下求娶,您,嫁還是不嫁?
99.5萬字8 29357 -
完結74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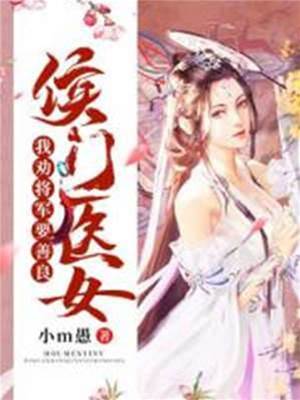
侯門醫女:我勸將軍要善良
被逼嫁給一個兇殘暴戾、離經叛道、罄竹難書的男人怎麼辦?顧希音表示:“弄死他,做寡婦。”徐令則嗬嗬冷笑:“你試試!”顧希音:“啊?怎麼是你!”此文又名(我的男人到底是誰)、(聽說夫人想殺我)以及(顧崽崽尋爹記)
127.2萬字8 52202 -
完結96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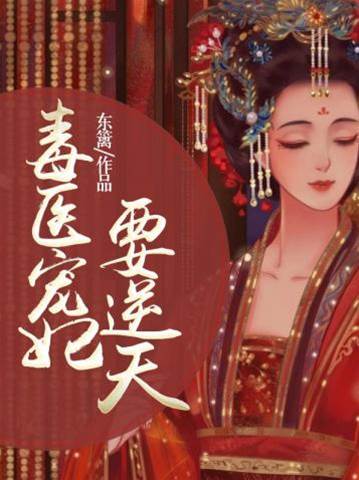
毒醫寵妃要逆天
為助他登上太子之位,她忍辱負重,嫁給自己最討厭的人。更是不顧危險,身披戰甲,戎裝上陣。 她癡心十年,等到的卻是他的背信棄義,殺害全家。 好在蒼天有眼,讓她重活一次,這一次她不僅要親手送他入地獄,更要與那個錯過的愛人,攜手稱霸這萬里山河。
100.5萬字8 19258 -
完結33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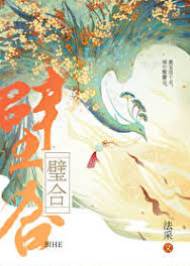
璧合
鄧如蘊來自鄉下,出身寒微,能嫁給西安府最年輕的將軍,誰不說一句,天上掉了餡餅,她哪來的好命? 鄧如蘊聽着這些話只是笑笑,從不解釋什麼。 她那夫君確實前程廣闊,年紀輕輕,就靠一己之力掌得兵權,他亦英俊神武,打馬自街上路過,沒人不多看兩眼。 鄧如蘊從前也曾在路邊仰望過他,也曾看着他頭戴紅纓、高坐馬上、得勝歸來的晃了眼,也曾,爲他動過一絲少女心絃... ... 如今她嫁給了他,旁人豔羨不已,都說她撞了大運。 只不過,當他在外打了勝仗而歸,從人群裏第一眼尋到她,便眸中放光地大步向她走來時,她卻悄悄退到了人群的最後面。 鄉下來的尋常姑娘,如何真的能給那樣前程廣闊的年輕將軍做妻? 這左不過是一場,連他也不知道的契約而已。 契成之日,他們姻緣結締;契約結束,她會如約和離。 她會留下和離書,從他的人生中離去,自此悄然沒入人海里。 * 那年鄧如蘊兩手空空,一貧如洗,沒法給年邁的外祖母養老,也沒錢給摔斷腿的姨母治病,還被鄉紳家的二世祖虎視眈眈。 這時將軍府的老夫人突然上了門來。老夫人問她願不願意“嫁”到滕家三年,只要事情順利完成,她可以得到滕家的庇佑和一大筆錢。 好似給風雪裏的人送上棉衣,鄧如蘊沒猶豫就應了下來。 她需要這筆錢。
51.4萬字8.17 241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