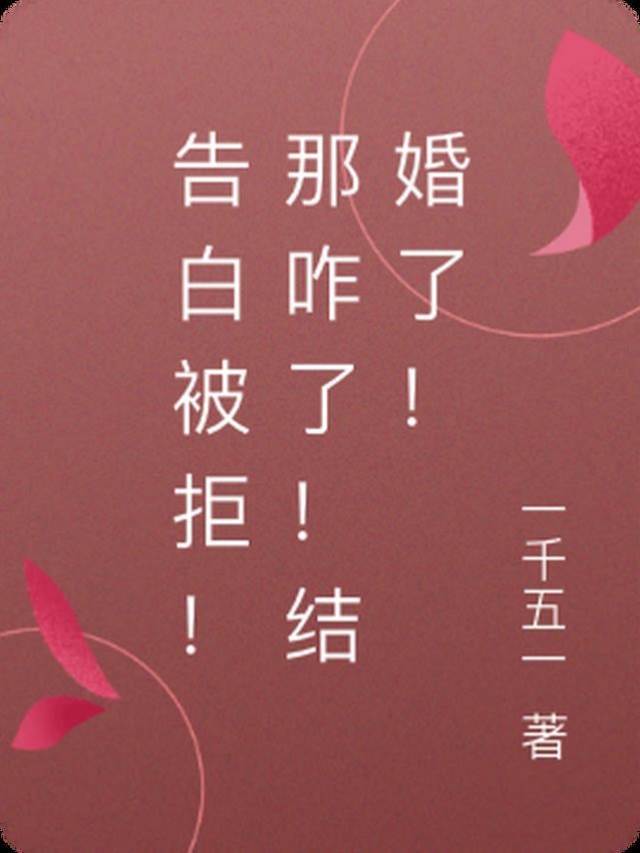《臣服》 第5章 罪有應得
將秀拳的攥住,抬眼看向秦順。
秦順角帶著一種不懷好意的笑,並沒有阻止的意思,宋綰便知道,這頓飯,恐怕沒那麽好吃。
宋綰在周遭的嘲諷中,朝著秦順看過去,良久,微微笑了笑,:“對不起,秦總,我來遲了,先自罰三杯。”
宋綰完,也不顧在場人是什麽反應,自行倒了酒,就自顧的喝了下去。
那酒是濃烈的白酒,喝到裏,咽下去的時候,就從裏一直燒到胃裏,並不好,但是再不好,也要比痛灼的心要好點,宋綰連著喝了三杯。
手指白皙瑩潤,又細長,拿著盛著酒的酒杯時,像是一件藝品,揚起頭喝酒時,漂亮的鎖骨凸顯出來,是真的讓人移不開眼。
就算坐了三年多的牢,也沒有讓這個人的姿打半分折扣,反而顯出一種不清的。
Advertisement
看著這樣果斷,在場的人反而沉默下來,男人的目本不控製的,盯住瓷白的,人的臉卻很難看。
不知道是誰開口:“以前聽宋姐為人清冷,別人敬酒從來不應,看來傳言也並不是很可信。”
宋綰皺了下眉,複又鬆開,再難堪的事,都已經經曆了。
宋綰垂了垂長長的眼睫,揚笑道:“以前是綰綰不懂事,如果哪裏有得罪各位的地方,綰綰在這裏給大家道個歉。”
酒在的胃裏灼燒得越發厲害,瓷白的臉上出一點緋紅,好像連那截漂亮的脖頸和鎖骨都罩上了緋,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瞳卻格外亮,像是盛著一汪清水。
將姿態放得那樣低,仿佛刀槍不,又得不可方,在場的人竟一時間忘了話。
Advertisement
還是秦順最先反應過來,哈哈哈大笑著道:“宋姐真是爽快,來來來,宋姐先在這裏坐,我給宋姐引薦一下,這位是盛名的卓總,這位是萬康的周總……這位是凱嘉的陳總……”
他一連介紹了好幾個,隻在介紹凱嘉的陳總時,宋綰的目凝了凝。
記得凱嘉和陸氏集團曾經發生過惡競爭。
不過,能背著陸薄川,打著幫的名義讓到這裏來,想來這些人也和陸薄川的關係不太好。
隻是有點怕。
宋綰和秦順介紹的人一一打了招呼,這才坐下來。
剛一坐下來,有個人便朝著問道:“我聽當年宋姐為了季家爺,可是做了很多駭人聽聞的事,又是為他打胎又是為他坐牢,季家如今勢力也不,宋姐不過就是給父親換個腎而已,季家難不連這點忙也不肯幫?還是,當年宋大姐不過是一場單相思?”
Advertisement
“還打過胎?不是吧?宋姐看起來本不像懷過孕的人啊。”
宋綰著酒杯的手指狠狠收,覺心髒被得難,關於那些事的新聞,在網上已經看了不知道多遍,勉強笑了笑:“大概這就罪有應得吧,怪不得別人。”
桌上的人今大概是專門來看笑話的,後來的問題一句比一句犀利,宋綰漸漸有些招架不住。
哪怕已經刀槍不,也會覺得疼。
“對不起,我去一趟洗手間。”宋綰終於承不住的時候,突然站了起來,搖搖晃晃的去到洗手間洗手。
喝得有點多,眼前幾乎要出現重影。
可是還是覺心髒像是被人挖了一樣難。
就像當初失去孩子的時候的那種覺。
所有人,包括,記者,都認為是引產了自己八個月大的孩子,可真像真的是這樣嗎?
宋綰咬住牙。
等再回到房間的時候,整個人卻是一愣。
因為在飯桌上,看到了一個絕對不可能看到的人。
猜你喜歡
-
完結288 章

分手后,病嬌大佬總掐我桃花
姜瓷18歲便跟了傅斯年。 做了他5年的秘密女友,卻等來他的一句:「我要結婚了」 後來,姜瓷死心了。 開始專心搞事業,在古玩界混得風生水起,追求者更是踏破門楣。 傅斯年卻怒了,權勢滔天的他,不僅掐盡她的桃花,還將她傷得體無完膚。 後來,姜瓷乘坐的輪船著火了。 傅斯年站在岸邊眼睜睜的看著大火將她吞噬。 臨死前姜瓷眼中滿含恨意。 「我寧願,不曾跟你有過一絲一縷的牽絆」 傅斯年終於慌了。 「姜瓷,你敢死,我就讓你在乎的人都為你陪葬」 姜瓷慘白的臉上掛著苦澀的笑,絕望又悲涼:「傅斯年,這一次你再也威脅不到我了」 失去姜瓷后,傅斯年徹底瘋了。 直到某一天,那個熟悉的身影挽著別的男人與他擦身而過……
52.6萬字8.18 21647 -
完結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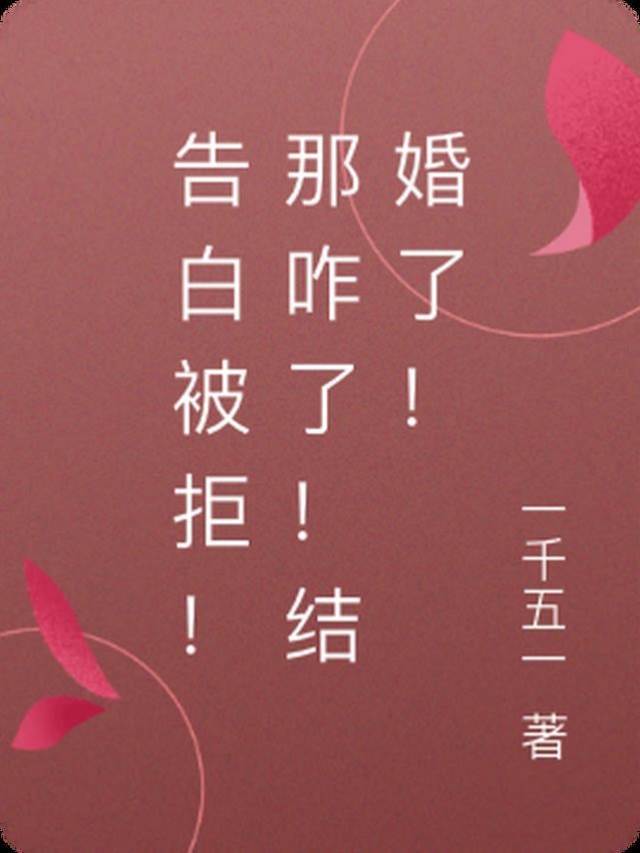
告白被拒!那咋了!結婚了!
【明著冷暗著騷男主VS明媚又慫但勇女主】(暗戀 雙潔 甜寵 豪門)蘇檸饞路遲緒許久,終於告白了——當著公司全高層的麵。然後被無情辭退。當晚她就撿漏把路遲緒給睡了,蘇檸覺得這波不虧。事發後,她準備跑路,一隻腳還沒踏上飛機,就被連人帶行李的綁了回來。36度的嘴說出讓人聽不懂的話:“結婚。”蘇檸:“腦子不好就去治。”後來,真結婚了。但是路遲緒出差了。蘇檸這麽過上了老公今晚不在家,喝酒蹦迪點男模,夜夜笙歌的瀟灑日子。直到某人提前回國,當場在酒店逮住蘇檸。“正好,這房開了不浪費。”蘇檸雙手被領帶捆在床頭,微微顫顫,後悔莫及。立意:見色起意,春風乍起。
26.9萬字8 9881 -
完結206 章

套路微微甜
不婚主義的程陽遇到了套路滿滿的蘇遇卿,開始他還有所抵抗,警告她:“別動不動就哄人啊,我不吃那套。”后來他就直接自我放棄了。 她問:“你想聽實話嗎?” 他說:“實話難聽嗎?” “有一點。” “那我還是聽甜言蜜語吧,要甜透了心的那種!”
38.5萬字8 14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