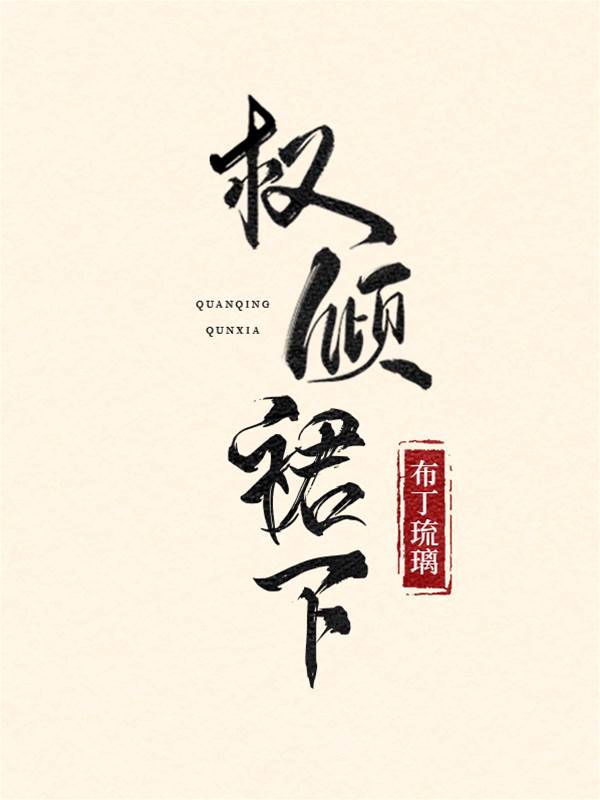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我見觀音》 第68頁
謝旻剛要應答。
這時,車簾被掀起了一角。
謝旻一看來人,面不善:“怎麼?馬車坐不下去了。”
耶律堯逆著,那張立分明的臉更顯桀驁不馴,嗤笑一聲:“誰要坐你馬車了?五個人,沒一個聽到貓落下了麼?”
隨著他話音剛落,那只漂亮矯捷的三花貓一躍而上。小貓被了好一會兒,像是有點委屈,著嗓子了幾聲,愣是沒敢直接躥宣榕懷中。
宣榕掏出帕子替它了,又聽見耶律堯似是詢問:“聽風閣?”
阿旻發脾氣發得如此明顯,宣榕本還以為耶律堯不樂意去,見他竟然追問,微微一怔:“對,在天機部的玲瓏寶塔附近,居山而立的那家。你若先到,報公主府名號即可。”
“好。”
*
聽風閣臨山而建,四面環空,與不遠的玲瓏寶塔對面相。
在此能聽風聲颯颯、松海濤濤、竹海瀟瀟。十年前閣出資建后,文人雅客都喜來此,留下不詩詞墨寶。
墻上掛山水畫、前人文,木質閣樓,一派清凈典雅。
Advertisement
此時,雅間,琴師在屏風后琴,琴音泠泠,如泉水清澈。
而沉默無言,似寒霜蔓延。
最后還是承吉打破僵局:“郡主,您方才說有話問我?是何方面的?”
傅承吉今年三十有六,留了一道山羊胡,儒雅中幾分工匠的嚴謹。
他十二歲天機部,在天機部算得上老資歷,任職右侍郎,平日隨侍謝旻左右。
宣榕瞥了眼自落座來,沒再互相看一眼的兩人,收回目,無奈道:“想問一問宋灼大人的況。今日路過賭坊,看他雙有恙……”
傅承吉聞弦知雅意:“哦郡主想問他為何殘疾?實不相瞞,他那雙自部以來,就是那樣了,據說小時候嫡母待,在大冬天把他扔進河里,凍壞了。他生母有人脈,花重金在天機部下屬的‘制司’定做假肢,多年下來,這孩子和天機部也了,后來便來了這邊。我們幾個上司知道他況,平日也不派重活給他。”
宣榕了然,又問謝旻:“阿旻,你今兒是還有什麼事?”
Advertisement
謝旻抬眸瞥了眼耶律堯方向,那意思不言而喻:外人在場,不方便說。
宣榕看他那神,便道:“明日我去天金闕見舅舅,楠楠也在宮里嗎?我給帶了點隨行所見的孤本,還有幾篇不錯的武籍,然后四的小暗也搜集了些許,應該會喜歡。”
宣榕口中的“楠楠”,正是“顧楠”。死去的如舒公顧弛之。
謝旻忽然默了默,半晌才道:“在。今兒找表姐,本來還想請你幫忙參謀一下,年節給挑點什麼禮比較好。”
宣榕溫聲道:“我帶的這些你可以拿去,借花獻佛。”
謝旻苦笑道:“不行啊榕姐姐。母后本就因為年居鐘南山,不喜歡,再讓撿起這些南山舊風……你這是要我的命啊。”
“可喜歡這些啊。”宣榕一頭霧水,“舅母喜不喜歡,有何用?”
謝旻抿,微不可查地吐出一句:“可我想娶。”
宣榕看著表弟苦大仇深的臉,將掌心茶杯一放,嚴肅問道:“娶,還是納?”
Advertisement
“……納。”
想來也知。顧弛在世時,未取得一半職,全靠名和真本事吸引一眾學子,顧家也勉強算有幾分資本和靠山。
如今如舒公已死,顧母早已過世。整個顧家,只有顧楠。
不可能為東宮真正的主人。
皇后也不會放任自己兒子娶一個娘家毫無助力的妻子。
“阿旻,你這是在瞎胡鬧。”宣榕蹙眉道,語調輕,呵斥也像安,很難讓人心生反,“你把拘在宮里,本就不妥了,聽說學規矩學得飛狗跳,痛苦得幾乎要上吊了。我倒是有個想法……”
謝旻抬眸:“你說。”
宣榕緩緩道:“放出宮,讓跟著昔大人闖幾年,多能長點見識、廣人脈。西方若有戰事,要是能靠此服眾,也有更大話語權來周旋博弈。”
謝旻斷然拒絕:“不行!!!一個滴滴的姑娘家,萬一有什麼損失,百年之后我無見老師……”
宣榕一臉無語看他:“如舒公早就說了不想兒嫁宮闈。你所做所想,就很有面見他了嗎……?”
Advertisement
謝旻被說得啞口無言。
宣榕眉梢微蹙:“早年你們都小,能算作兄妹相,尚好,如今京中已有閑言碎語,說顧楠是你的人,日后怎麼自?”
謝旻沉默。
宣榕又道:“況且,權力這種東西,意味說話分量。你連獲得這些的機會都不給楠楠,還指舅母放你們圓滿?”
“它也意味著勞累、痛苦、傾軋、泯滅人。”謝敏低低道,“很累很臟,我不想讓沾這些。”
是這樣的。一切權力的獲得,都注定不那麼太平愉快。
它伴生出來的責任人,伴隨出來的害人,伴同出來的爭斗折磨人。
宣榕卻不置可否:“你怎知不能適應這些?”
謝旻垂下眼簾,輕咬下,生生轉了話題:“不知道。對了姐,你給帶了那麼多東西,我呢?給我帶什麼了?”
小士: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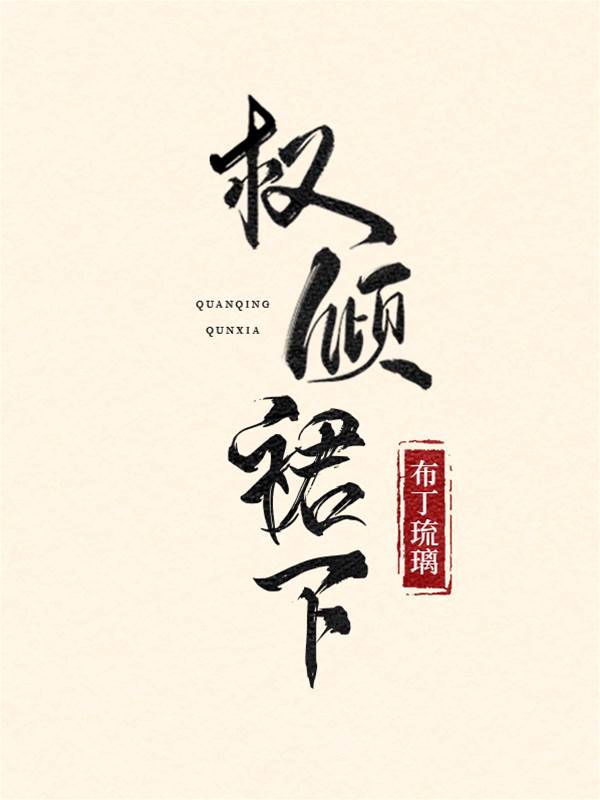
權傾裙下
太子死了,大玄朝絕了後。叛軍兵臨城下。為了穩住局勢,查清孿生兄長的死因,長風公主趙嫣不得不換上男裝,扮起了迎風咯血的東宮太子。入東宮的那夜,皇后萬般叮囑:“肅王身為本朝唯一一位異姓王,把控朝野多年、擁兵自重,其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聽得趙嫣將馬甲捂了又捂,日日如履薄冰。直到某日,趙嫣遭人暗算。醒來後一片荒唐,而那位權傾天下的肅王殿下,正披髮散衣在側,俊美微挑的眼睛慵懶而又危險。完了!趙嫣腦子一片空白,轉身就跑。下一刻,衣帶被勾住。肅王嗤了聲,嗓音染上不悅:“這就跑,不好吧?”“小太子”墨髮披散,白著臉磕巴道:“我……我去閱奏摺。”“好啊。”男人不急不緩地勾著她的髮絲,低啞道,“殿下閱奏摺,臣閱殿下。” 世人皆道天生反骨、桀驁不馴的肅王殿下轉了性,不搞事不造反,卻迷上了輔佐太子。日日留宿東宮不說,還與太子同榻抵足而眠。誰料一朝事發,東宮太子竟然是女兒身,女扮男裝為禍朝綱。滿朝嘩然,眾人皆猜想肅王會抓住這個機會,推翻帝權取而代之。卻不料朝堂問審,一身玄黑大氅的肅王當著文武百官的面俯身垂首,伸臂搭住少女纖細的指尖。“別怕,朝前走。”他嗓音肅殺而又可靠,淡淡道,“人若妄議,臣便殺了那人;天若阻攔,臣便反了這天。”
52.5萬字8 22512 -
完結967 章
神醫王妃她拽翻天了
秦語穿越成炮灰女配,一來就遇極品神秘美男。 秦語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因為相遇是妹妹陷害,大好婚約,也不過是她的催命符。 秦語輕笑:渣渣們,顫抖吧! 誰知那令人聞風喪膽的燕王,卻整天黏在她身邊.
170.1萬字8 23384 -
完結161 章

太子妃實在美麗
尚書府的六姑娘姜荔雪實在貌美,白雪面孔,粉肌玉質,賞花宴上的驚鴻一現,不久之後便得皇后賜婚入了東宮。 只是聽說太子殿下不好女色,弱冠之年,東宮裏連個侍妾都沒養,貴女們一邊羨慕姜荔雪,一邊等着看她的笑話。 * 洞房花燭夜,太子謝珣擰着眉頭挑開了新娘的蓋頭,對上一張過分美麗的臉,紅脣微張,眼神清澈而迷茫。 謝珣:平平無奇的美人罷了,不喜歡。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晚上,她換上一身薄如蟬翼的輕紗,紅着臉磨磨蹭蹭來到他的面前,笨手笨腳地撩撥他。 謝珣沉眸看着她胡鬧,而後拂袖離開。 謝珣與她分房而睡的第三個月,她遲遲沒來, 謝珣闔目裝睡,等得有些不耐煩:她怎麼還不來撩孤? * 偏殿耳房中,姜荔雪正埋頭製作通草花,貼身宮女又一次提醒她:主子,太子殿下已經到寢殿好一會兒了。 滿桌的紛亂中擡起一張玉琢似的小臉,姜荔雪鼓了鼓雪腮,不情願道:好吧,我去把他噁心走了再回來… 窗外偷聽的謝珣:……
25.7萬字8 769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