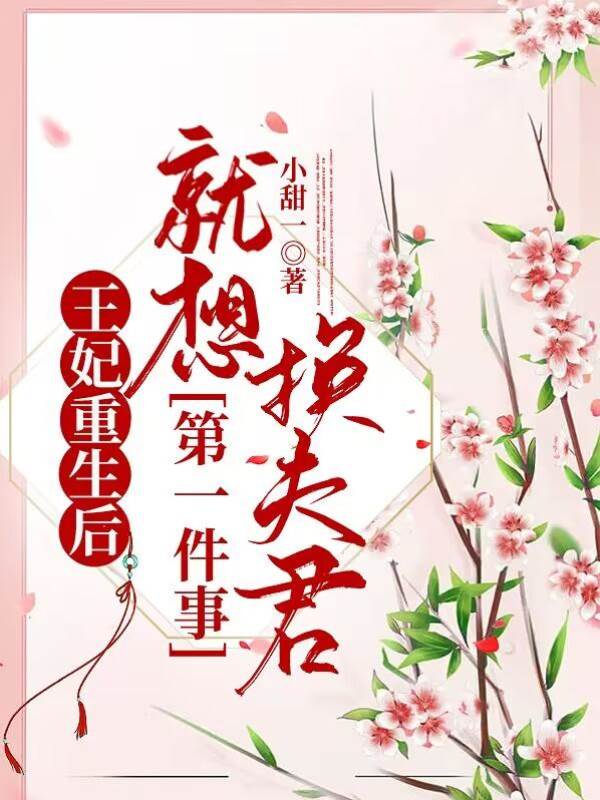《春枝纏》 聘金
聘金
“自然不會……”
謝昀截斷的話, 又追問了句:“當真?”
羅紈之後知後,著謝昀,微蹙起眉:“郎君, 你是病了嗎?”
若不是病了, 怎麽會這樣離不開人,又不是三歲的小娃娃。
“嗯, 病了。”
羅紈之手了下他的額頭, 溫度還沒有的手心高, “沒有發熱。”
“病只有風寒發熱一種嗎?”
“那三郎是哪裏不舒服了?”
“心不舒服。”
“……”羅紈之看著他不做聲, 只用眼神示意:願聞其詳。
謝昀也不賣關子:
“早晨婆上門要與我說親的時候,你為何在旁邊問那郎家底不厚?”
“……好奇。”
“那問起家裏的床是不是黃檀木的原因?”
“也是好奇!”
謝昀促笑了聲,手指順著袖子就握住的手腕,把拉近,眸稍瞇, 低聲問:“你莫不是就想反悔不‘養’我了?”
他說得自然, 但羅紈之聽得臉皮都要發燙, 認真糾正他:“三郎幫我做事,我給三郎發工錢, 天經地義,說起來也是三郎自力更生養活自己了!”
天知道多後悔說出“我養你”那句話,現在謝三郎日日跟著,搞得同行表面旁敲,背後瞎傳,說養了個男寵……
可這哪是男寵, 分明是祖宗。
“總而言之……”羅紈之把自己的手腕了出來, “三郎不用靠著誰,也能過得很好……”
前提是不要再想什麽黃檀木的床了。
真的很貴!
“你若是不想養我, 我也可以養你。”謝昀任收回手,眼眸一彎,長睫也難掩眼底的真實意,發著璀璨的芒。
羅紈之心尖微,就像是被輕敲的琴弦,餘音。
“……郎君哪有錢?”也不是那麽容易就打發的。
Advertisement
“方法總是有的,只是,你答應了嗎?”
羅紈之故意曲解他的意思:“郎君現在能賺到的錢,我自己也能賺。”
換言之,不用靠著他了。
“你知道我不是這個意思。”謝昀這次不想讓蒙混過關,認真道:“我們之間并無阻礙,而我想娶你,也是真心實意的。”
羅紈之後背發麻,耳尖也逐漸滾燙,努力鎮定道:“安南婚嫁的聘金可不是小數目,郎君要想娶妻非得攢個十年八年才能夠吧。”
“再說了,我現在并不想嫁任何人。”
*
到了安南商行的局會。
周圍的人都在激烈地討論,唯有羅紈之撐著腮發呆。
面前的窄口寬肚瓶裏正好斜了一枝桃花,上頭為數不多的花瓣剛被拍桌子的仁兄震掉了幾片,如今正沮喪地垂著腦袋。
越看越覺得那枝垂頭喪氣的桃花像是被再次拒絕的謝三郎。
真是怪了!
羅紈之猛地晃了晃腦袋。
“看吧!我就說月大家雖是一介流,但就是比你們這些人眼長遠!”
羅紈之回過神,見在座的人都齊刷刷轉過腦袋當看猴一樣看著。
還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提起神環顧左右,“抱歉……”
“哼!都道如今生意難做正是因為北胡的緣故,你們居然還想著和他們做生意,莫不是嫌命長!”先前說話的人又激地拍了拍桌子,還不忘拉攏羅紈之道:“月大家你是個明白人,這與虎謀皮等同于羊虎口,是不是啊?”
不等羅紈之回答,旁邊的商人就撥弄著自己的金算盤,打得“劈啪”作響,口裏淡淡道:“和誰做生意不是做生意,只要有錢賺,沒人會嫌多。”
有人支持他就幫著說話,連忙道:“那位江枕眠,曾經可是建康鼎鼎有名的名士江老,如今就是北胡的重臣,赫拔都依靠他打通商路,所以才給我們讓了不利,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啊!”
Advertisement
最開始反對的那商賈難掩鄙夷:“我怕你們都忘記了嚴舟的前車之鑒了吧?不但家産抄沒,人還在大牢裏蹲著……他和北胡共謀的時候可比你我早多了,出了事有人來保他嗎?有人嗎?”
“別提嚴舟了,嚴舟那是被謝家盯上了。謝家宰了羊好過年罷了,你看我們這才哪到哪,連他一個腳指頭都比不上,謝家也不指我們這點錢過活吧!”對方不在意,擺擺手道:“我知道錢兄一直以來做事謹慎,但是我們今天只是把好機會放出來一起討論,沒道理你不願意也礙著別人做吧?”
羅紈之聽到這裏方明白他們在吵什麽。
自從嚴舟倒臺後,北胡一時沒有找到可靠的渠道運輸購買北境稀缺的各種品,所以通過晉臣的人脈在這些商賈裏面挑選。
安南的商賈自一圈,遇大事總要討論一番,也免得誰多吃了虧,誰獨霸鰲頭。
“先前錢公說的有理,北胡與我大晉關系還不穩定,誰也知道他們實際打的是什麽主意,進去容易,再想摘出來卻難了……”羅紈之搖搖頭,表達了自己的觀念:“我不求大富大貴,只想過得平平穩穩。”
好好活著,平平安安才是最重要的,錢多到一定程度,反而是種負累,就比如嚴舟。
他手上不幹淨是真的,謝家想要整他也不假,要不然也不會在短短時間裏就把他的家産搜刮一空,就連那些藏得深的地方也一幹二淨。
嚴嶠回信給說。
謝家分明是早做了打算,才得一清二楚。
深以為然。
因為正是謝昀一步步把嚴舟引到那深淵裏。
“月大家稍安勿躁,咱們還好商量嘛!”對這件事最熱衷的一位商賈馬上給羅紈之倒茶留人,著手熱道:“這次的機會實在難得,月大家你有船也有商路,最適合不過了,所謂富貴險中求,賺錢哪有沒風險的……”
Advertisement
羅紈之會被奉為座上賓也在于此。
有實力的商賈,要不有大量資産,要不有完善的商路,其他的小商賈要想賺錢只能搭上他們的東風。
羅紈之還是搖頭,正道:“這些世之財我不想,也不想牽連進去,諸位知道我的來歷,我阿翁年事已高,不了再多的打擊,此生不求富貴顯榮,只願與家人平安度過餘生。”
幾名商賈面面相覷。
羅紈之又起,笑著賠禮道:“當然,若有其他機會,我還是很願意與諸位前輩共商同議。”
這句話稍稍讓其他商賈心裏好了些。
不是這郎自視甚高,不願意和他們合作,而是膽小怕事罷了。
畢竟只是個郎嘛!
不過也不是所有人都被三言兩語給安好了。
有人就怪聲怪氣道:“說到穩妥,近來安南打算組織剿匪,賞金厚啊!月大家可是心這個?”
“剿匪?”羅紈之怎麽聽不出對方故意戲謔,不過只裝作不知道,還好奇問:“不想安南無兒郎,連郎也肯用,當真是一視同仁,好極。”
那人一哽,角。
好個牙尖利的郎,還罵他不是男兒。
錢公把羅紈之當作自己這一派,大力維護,朝那不懷好意的人啐了聲,“安南的匪患已經有七八年,坐山稱王,橫行霸道,兇悍無比,這次招募的都是游俠好漢,去前還要簽生死狀,這種于民有益的t好事,豈能當作兒戲議論!”
“這樣厲害啊,都要簽生死狀,這錢可不好賺……”有人驚呼。
“要不然怎麽說賞金厚,只有缺錢的人才會冒著生命危險去幹……”錢公的話兜兜轉轉又在點明自己的主張。
有些事就是錢再多,也不值得搭上命!
到了掌燈時分,羅紈之總算得以,乘著犢車往家回。疲憊的懶洋洋靠在車壁上,還打算趁機休息一下,不想突然間,車夫勒停車,慣讓羅紈之險些磕破腦袋。
Advertisement
驟然驚醒,扶著把手問:“發生何事了?”
車夫在外面道:“無事,只是遇到一隊傷員趕著救治……”
羅紈之開車簾,就聽見一陣陣低的嗚咽哭聲,伴隨著幾個被擡走的春凳疾步逐漸遠去。
“他們這是?”
車夫慨道:“那些躺著的都是跟去剿匪的人,這次傷亡如此慘重卻未能功,只怕剿匪的賞金還要提一提,不然後頭誰人還敢去!”
顯然這不是安南第一次剿匪。
那些橫行霸道的山匪占據了有利地勢,對往來的商隊、行人肆意搶掠,是安南的沉疴痼疾,危害已久。
羅紈之目睹那些哭得快要昏倒的傷員親人,上穿著帶著補丁的樸素布,有些還牽著抱著幾個大小不一的孩子,每一個都是滿臉悲愴,痛不生。
倘若不是為了生活,為了錢,們的親人也不用以涉險。
如今們失去的不僅僅是厚的賞金,還有家中到頂梁柱。
無論如何,羅紈之也不想把自己送到危險的地方。
不管遠一點南北張的局面,還是近一些的山匪橫行,這些都是大事,但也都是管不了的事。
眼下,只有獨善其才能過得安穩。
回到宅子,羅紈之看見謝昀居然也在,霍十郎不知道與他在說些什麽,看見面就打住了聲音,笑瞇瞇對一揮手,然後一溜煙跑走了。
“怎麽這麽久?”謝昀回頭問,語氣平緩,“是遇到了難事嗎?”
羅紈之張了張,想到嚴舟的下場就是眼前這位郎君的傑作,再說他現在既然已經離開謝家,這些事也與他沒有關系。
“沒什麽,你和霍十郎在聊什麽?”
謝昀拿剛剛的話回:“沒什麽。”
羅紈之哼了聲。
學人。
羅紈之徑直走回自己的屋,發現楊媼已經把飯菜做好,并用網蓋在了桌子上。
楊媼知道不喜歡吃安南菜,特意學了豫州的菜系,即便出門去應酬,也會給留幾樣墊肚子,免得在外面沒吃飽要空著肚子睡覺。
羅紈之一直沒聽見後離開的腳步聲,知道謝昀就在原地沒走,遂回頭問他:“郎君用晚飯了嗎?”
蛐蛐藏在草叢裏,幾盞燈孔照亮了庭院,也照亮了郎君的笑容。
“沒有。”
“要吃嗎?”
“吃。”
就知道!
羅紈之抿了下,又輕輕咬住,角卻沒有忍住稍稍揚起,提起擺進門檻。
後邊的腳步聲隨而來,不不慢,卻越來越近。
生活要是一直這樣平淡簡單,也未嘗不可。
過了幾日。
果如車夫所料,安南把招募剿匪的賞金又往上提了一倍。
雖然上一批人的慘烈結局尚在眼前,但新的壯丁還是為那賞金眼紅,踴躍報名。
等到他們又組織了一批人上山,羅紈之在關注剿匪消息的同時,也在奇怪已經有兩日沒有再見到謝昀了。
要知道,這些時日,不管有事沒事,謝昀都會常在眼皮底下晃。
可這次忙過頭後,一想,竟如此反常。
更巧的是,霍十郎也不見蹤影。
羅紈之去了隔壁宅子,在書房裏果然看見謝昀留給的信。
只有短短一行字:“賞金厚,能聘我妻,等我。”
猜你喜歡
-
完結1698 章

農門凰女
他是村裡最年輕的秀才,娶她進門,疼她、寵她、教她做一個無所畏懼的悍妻,對付糾纏不清的極品親戚。
310.4萬字8 83298 -
完結852 章

我見探花多嬌媚
靖寶有三個愿望:一:守住大房的家產;二:進國子監,中探花,光宗耀祖;三: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顧大人也有三個愿望:一:幫某人守住家產;二:幫某人中探花;三:幫某人將女扮男裝進行到底!…
146.8萬字8 32660 -
完結1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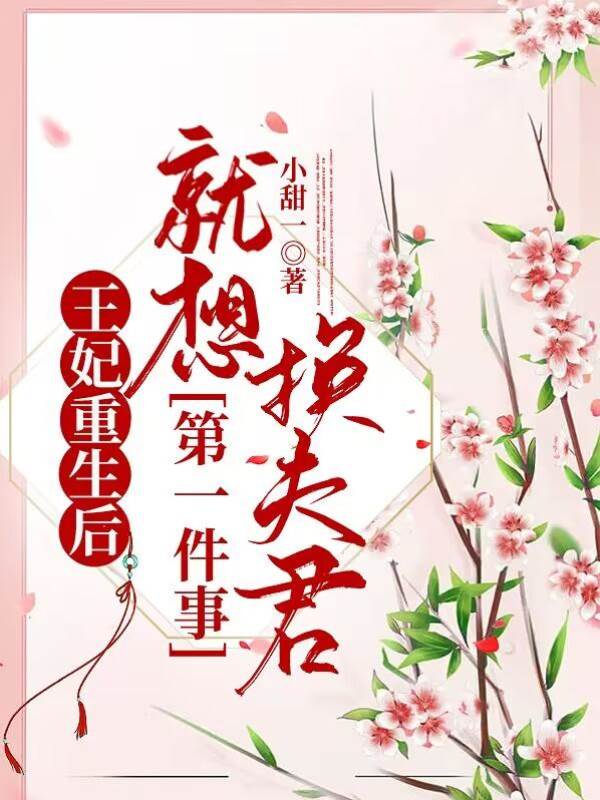
王妃重生後,第一件事就想換夫君
上輩子盛年死於肺癆的昭王妃蘇妧重生了。回想自己前一世,溫婉賢惠,端方持家,一心想把那個冰塊一樣的夫君的心捂熱,結果可想而知;非但沒把冰塊捂化了,反而累的自己年紀輕輕一身毛病,最後還英年早逝;重生一世,蘇妧仔細謹慎的考慮了很久,覺得前世的自己有點矯情,明明有錢有權有娃,還要什麼男人?她剛動了那麼一丟丟想換人的心思,沒成想前世的那個冤家居然也重生了!PS:①日常種田文,②寫男女主,也有男女主的兄弟姐妹③微宅鬥,不虐,就是讓兩個前世沒長嘴的家夥這輩子好好談戀愛好好在一起!(雷者慎入)④雙方都沒有原則性問題!
34.3萬字8 20883 -
完結105 章

夫君他竟然
沈訴訴夢見未來,差點被自己的夢嚇死。 她將會被送入宮中,因爲被寵壞,腦子不太好,她在宮鬥裏被陷害得死去活來。 後來她就黑化了,手撕貴妃腳踩原皇后成爲宮鬥冠軍。 但那有什麼用呢? 後來皇帝統治被推翻,她只當了三天皇后。 最後她死於戰火之中,三十歲都沒活過。 驚醒過來的沈訴訴馬上跑路,不進宮,死也不進宮! 她的縣令爹告訴沈訴訴,你生得好看,不嫁人遲早要入宮。 沈訴訴環顧四周,發現自己身邊那個沉默寡言的侍衛不錯。 這侍衛長得帥身材好,還失憶了,看起來就很好拿捏。 之前沈訴訴機緣巧合把他救下,是他報恩的時候了。 沈訴訴和帥氣侍衛商量着要不咱倆搭夥假成親算了。 侍衛烏黑深邃的眼眸盯着她說了聲好。 沈訴訴下嫁府中侍衛,成爲坊間一大笑談。 她本人倒是不在意這些,畢竟她家侍衛夫君話少還聽話。 沈訴訴性子驕縱,壞事沒少幹,上房揭別人家瓦時,墊腳的石頭都是他搬來的。 她身子弱,時常手腳冰涼,她把他當暖爐,抱着睡一整夜,他也毫無怨言。 她要吃城西的熱乎糕點,他施展常人所不能及的絕佳輕功,回來的時候糕點還是燙的。 沈訴訴過了幾年快活日子,後來江南有禍事起,叛軍要推翻朝廷。 這也在沈訴訴的預料之中,她準備叫上自己老爹和夫君一起跑路。 但她的侍衛夫君不見蹤影,沈訴訴氣得邊跑邊罵他。 她一路跑,後面叛軍隊伍一路追,沈訴訴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他們啥了。 最後她沒能跑過,被亂軍包圍。 爲首鐵騎之上,銀甲的將軍朝她伸出手,將她抱到馬上。 沈訴訴麻了,因爲該死的……這個叛軍首領就是她夫君。 難怪追殺(劃掉)了她一路。
15.5萬字8 21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