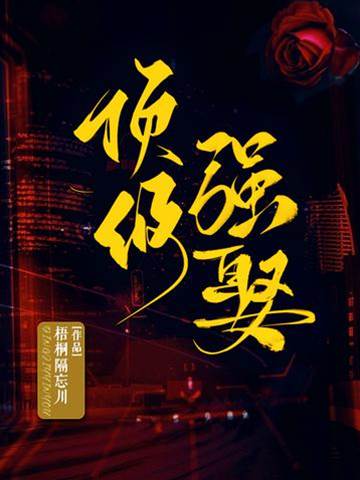《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第2卷 番外2 婚前焦慮癥
领证的前一个月,盛祁开始失眠了。
他反复问阮时音:“你爱我吗?”
阮时音哭笑不得,不明白都到今天这地步了,他怎么还会担心这个问题。
盛祁却不依不饶:“你是不是因为动才和我在一起的?你会不会后悔?”
阮时音说不是,不会后悔。
他又问:“你会不会以后就不爱我了?”
说到这儿,盛祁突然反应过来:“阮时音,我才发现,你居然从来没说过我爱你。”
“……”
于是那天晚上,阮时音在他下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我爱你,嗓子都快哑了才把人哄好。
抚很有用,盛祁焦虑的绪终于没那么明显,但是,他开始变得黏人了。
白天任何空隙时间都形影不离,晚上常被他折腾到大半夜。
一开始阮时音顾及他的绪,没及时停,结果就是变本加厉,盛祁连上课都想跟着,而且晚上…
阮时音腰酸背痛地委婉拒绝,好言相劝:“我一进学校就一直在风口浪尖,不想谈个爱又弄得这么高调,你也不想我被人在后面说三道四吧?”
“还有,年纪轻轻的,不要纵,不然以后老了就知道了。”
盛祁对前面的话很认同,后面那句嗤之以鼻。
“阮时音,你迟早会为你的质疑到愧。”
“好好好,我愧,但是现在不能再这样了。”
有苦难言。
哪怕没了翃,盛祁体质也真的有点超常,已尽量配合,但实在是跟不上。
节假日还好,第二天能睡到自然醒。
但现在需要上课,不能再这样惯着他了。
盛祁点头同意,表示自己会努力控制。
白天还是像以往一样,接人,吃饭,送人。
晚上就会困难很多,阮时音查资料的时候,他要搂着,也不做什么,就头靠在上,不言不语的,时不时轻嗅一下。
Advertisement
阮时音洗澡的时候,他要守在外面,懒洋洋地靠在墙边,听水声。且这已是努力以后的结果,按照以往早就冲进去了。
到睡觉的时候,阮时音怕他难,提出要分开睡。
盛祁顿时委屈得不行:“我都这么努力了,你还要跟我分居?”
“……”
阮时音说:“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
“不,我死也不要分开睡。”
于是便不分开,但同在一床,盛祁本忍不住不靠近。
一开始是悄悄牵住手,而后就开始搂腰,最后整个人都贴了上来。
他的呼吸灼热又急促,上的反应也太明显,阮时音无法当做什么都不知道。
但头不能开,不然白天的话都白说了。
盛祁被赶去浴室洗冷水澡,回来之后像只颓靡的巨型犬,轰地倒在床上,蜷起来,不说话了。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焦虑又变严重了。
盛祁自己心里也知道阮时音只是体有些不住,但毕竟还是缺了安抚,一些绪控制不住的冒了出来。
他开始头痛,闷,食下降,失眠更是家常便饭。
阮时音觉得这样不是办法,提出要带他去看医生。
但是这么科学的解决方式不知道怎么就被他理解了嫌弃。
一场微小争论过后,盛祁离家出走了。
放学没见到人来接,打电话发消息也无人响应。
阮时音自己回到家,花了大半个小时才接这个现实,又好气又好笑。
此时已天黑,打了所有可能找到他的电话,一无所获。
阮时音开始真的生气了,直接发了一条信息。
“再不回消息,我现在就搬走。”
十秒钟后,手机里弹出一条:“钟。”
……
山上的庄园已很久没人住,只留了几个看守和打扫的人。
一路赶到庄园,所幸里面的人都还认识,给开了门。
Advertisement
阮时音又风风火火地前往钟。
登上电梯,阮时音开始脱服,松开头发。
手速飞快,干脆利落,眸子里都是火星。
电梯门开,外面一片漆黑。
阮时音大步走出去,借着手机灯开始在屋内寻找,很快,看到了阳台外上坐着的人。
其实不用灯也能看清他了。
盛祁一条曲着,一条垂在半空,含着烟,沐浴月,看着外面的山林,一点猩红明明灭灭。
隔着一层玻璃门,他没有发现阮时音已到了,朝着半空吐了一口烟,烟像雾一样散开。
阮时音手机一关,把玻璃门用力拉开,声音很大。
盛祁立刻回头,脸上的泪痕在月下反了一瞬。
阮时音愣了一秒,紧抿了下,继续朝他快步走过去。
他微动,似乎刚想说什么,阮时音上前把他上的烟一拿,摁灭,随意一扔,然后扯他领。
“坐这儿?不要命了?”
气势汹汹,盛祁本说不出话,眼睛定在只有内的上半,看直了。
月下,孩白皙的皮肤泛着如玉的泽,骨骼纤细,材匀称。
盛祁结动,咽下口水。
阮时音把他扯下来,盛祁弯着腰,弓着背,乖乖地被拽到房间里。
把人往床上一扔,阮时音用手抚去他脸上残留的泪,吧唧亲了一口,然后面无表地开始他。
“阮时音。”
他想说话,却被一只手捂住。
阮时音躬靠近,语气危险:“安静点。”
他瞬间消音。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只有的声。
盛祁仰面躺着,呼吸逐渐重。
没有开灯,眼前只有一个模糊的廓,但那影是他日思夜想的,无比悉的。
他知道每一个曲线的弧度,知道每一个部位的软度,也知道不同位置温度的差异。
Advertisement
他很难,但不敢说话,直到看到阮时音俯低头。
“阮…”
“闭。”阮时音把头发塞到耳后。
床单被抓到变形。
这是一次无与比的体。
阮时音一改往日的模样,一手主导,但明显心还有不佳,除了偶尔冷淡地骂他再没有说过其他话。
盛祁只觉在体里快速流窜,大脑发懵。
似有幻觉。
狂风骤雨不歇,雷鸣闪电不止。
他的心在却在汹涌波涛中逐渐安宁。
很久以后,屋里再次安静下来。
阮时音汗涔涔地趴在他上,没有商量余地的语气:“明天跟我去医院。”
盛祁呼吸还没平复,手搭在背上,在黑暗中笑得牙不见眼。
“遵命。”
盛祁患了婚前焦虑症这件事不胫而走,赵子期得知这件事差点被笑死。
这跟阮时音无关,主要是盛祁本人表现得太明显。
赵子期笑得眼泪直飙:“时音,你不知道,他那天哈哈哈哈,他那天看到一对老夫妻,直接上去问人家白头到老的诀是什么,脸又臭,差点把人家老婆婆吓着,老爷子拐都要举起来了哈哈哈哈。”
盛祁龇牙:“找死啊你?”
阮时音给他顺:“没事,以后也会有年轻人来问你这个问题的。”
这个回答盛祁非常用,脸好转。
赵子期肩膀顶了顶旁边的邱喻白和秦放,悄悄说:“兄弟们,谈爱这么可怕吗?你看阿祁那样,哪还有半点以前的样子?”
邱喻白微笑:“我觉得好的,看起来很幸福。”
秦放照常发挥:“怎么没有以前的样子?他骂你的样子一点没变。”
赵子期:“我他喵的!”
……
由于阮时音那晚的破釜沉舟行动,再加上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不到一个星期,盛祁的症状明显好转。
Advertisement
最大的好转表现在睡眠上。
这一晚,他比阮时音早睡着。
暖的床头灯下,盛祁闭着眼睛,睫撒下影。
他呼吸很轻,表放松,看起来睡得很舒服,很沉。
已很久没有这样睡过一个觉了。
阮时音在旁边看着,心里酸疼。
其实没有想到,一路走来这么久,盛祁居然还会犯这种病。
一开始,以为是他对两人的不够有信心,但和医生流后,深想了很多。
事实上,盛祁无论是在格还是外表,都与刚刚认识的时候差不多。
他不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相反,很多时候可以说得上是傲慢。
他只是面对,不一样。
因为爱,所以害怕,因为害怕,所以无法维持自信。
如果非要分出个高低,阮时音觉得,盛祁应该更爱。
眼眶湿润。
何德何能,得此一人。
想到盛祁之前的抱怨,阮时音俯,轻轻抱住他。
“我爱你。”在耳边说。
别害怕,我会永远爱你。
猜你喜歡
-
完結97 章
不二之臣
盛夏夜裏暴雨如注,閃電撕扯開層層烏雲,悶雷緊隨其後,轟隆作響。帝都油畫院,中世紀教堂風格的玻璃彩色花窗氤氳出內裏的通明燈火,《零度》今晚要在這裏舉辦一場紀念創刊十周年的時尚慈善晚宴。宴前有一場談話會.....
30.4萬字8 28859 -
完結54 章

最深念想
十六歲那年,檀茉初見謝祁琛,男生白衣黑褲站在香樟樹下,面色清潤,望向她的眼底帶著溫柔笑意。她心跳如小鹿亂撞,然而對方始終把她當妹妹照顧,暗戀太酸澀,她還是選擇了放棄。多年后,當她長大,男人已然站在了名利場的中心位,傳聞他在商場上手段薄情狠辣…
27.3萬字8 18258 -
連載47 章
男神
穿制服的男人,總有一款是你的菜
54.8萬字8 13352 -
完結2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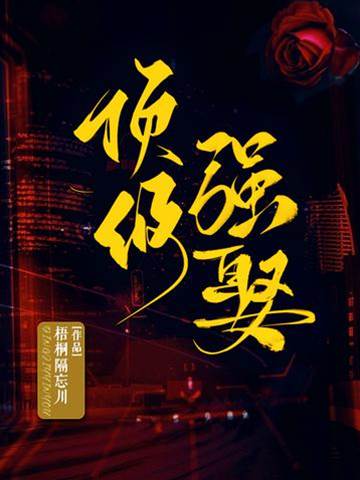
頂級強娶
【大女主?替嫁閃婚?先婚後愛?女主輕微野?前任火葬場直接送監獄?男女主有嘴?1v1雙潔?暖寵文】被未婚夫當街摔傷怎麼辦?池念:站起來,揍他!前未婚夫企圖下藥用強挽回感情怎麼辦?池念:報警,打官司,送他進去!前未婚夫的父親用換臉視頻威脅怎麼辦?池念:一起送進去!*堂姐逃婚,家裏將池念賠給堂姐的未婚夫。初見樓西晏,他坐在輪椅上,白襯衫上濺滿了五顏六色的顏料。他問她,“蕭家將你賠給我,如果結婚,婚後你會摁著我錘嗎?”一場閃婚,池念對樓西晏說,“我在外麵生活了十八年,豪門貴女應該有的禮儀和規矩不大懂,你看不慣可以提,我盡量裝出來。”後來,池念好奇問樓西晏,“你當初怎麼就答應蕭家,將我賠給你的?”他吻她額頭,“我看到你從地上爬起來,摁著前任哥就錘,我覺得你好帥,我的心也一下跳得好快。”*樓西晏是用了手段強行娶到池念的。婚後,他使勁對池念好。尊重她,心疼她,順從她,甚至坦白自己一見鍾情後為了娶到她而使的雷霆手段。池念問,“如果我現在要走,你會攔嗎?”“不會,我強娶,但不會豪奪。”再後來,池念才終於明白樓西晏的布局,他最頂級強娶手段,是用尊重和愛包圍了她……
51.8萬字8.25 37689 -
完結219 章

離婚后,京圈太子爺夜夜哭紅眼
結婚時,蘇黎本以為裴妄是愛她的,畢竟男人從不抗拒親密。她只想要一個孩子,可裴妄一直推諉,甚至告訴蘇黎:“我們永遠不可能有孩子!”不就是個孩子嗎?她找別人也能生!蘇黎將離婚協議送給裴妄,可是男人態度卻變了。“生,只和你生,不離婚好不好……”
40.9萬字8 11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