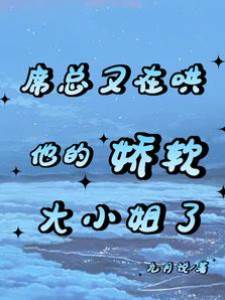《誘她入懷,聞少放肆寵》 第1卷 第56章 你還真不客氣,這就上手了?
別別扭扭吃完一頓飯,在柏叔的再三叮囑下,兩人一前一后上了樓。
常燈收拾完,從浴室出來時,發現聞柏崇還坐在沙發上,視線一直跟著走。
想起晚飯前他擰地提出的建議,也覺有點不自然了。
“你老看著我做什麼?”常燈指尖揪著擺,剛涂上的藥膏散發著淡淡的苦味,臉頰兩側涼涼的,“怪嚇人的。”
“我說的話你認真聽了嗎?”
聞柏崇直直看著,燈從頭頂灑泄,碎發微,臉部線條流暢,棱角分明,薄聳鼻,眼神帶著些許侵略,又像在試探著。
常燈回想起,輕點了點頭:“考慮過。”
“同意嗎?”
聞柏崇說反正兩人相舒適的,倒不如就這麼繼續下去,何必把自己變二婚,更何況,一旦離婚,聞老爺子肯定想方設法地再給他塞其他人,而且,他需要的幫助來從老爺子那拿到落湖居的另一半權,同時,保持這段婚姻,常燈也不需要有后顧之憂,需要的時候,他可以提供幫助。
總而言之,就是互贏。
常燈泰然自若,真的考慮好一會兒,才掀起眼皮子看過去:“你不會覺得我占了你的便宜嗎?”
畢竟,家世相差懸殊,他能提供給的價值,遠比能反饋的多的多。
“你也會妄自菲薄?”聞柏崇抬抬下頜,“別謙虛,你的閃點也很多。”
Advertisement
常燈不好意思地頭:“比如?”
“比如,眼獨到,最丑的兩條魚被你買回來了。”
“……”
聞柏崇見變了臉,好心地沒再損,反而破天荒地安兩句:“沒事,看魚的眼不行,看人的眼行就完事了。”
這意思就是在自夸。
“真自啊。”常燈躺床上,拉起毯子將自己遮的嚴實,不再理他。
聞柏崇也沒再繼續,許是累了,難得老實地窩在沙發上,兩人在微弱的線下慢慢眠。
夜半。
室一片幽靜,常燈睡足一覺,自然地睜開了眼。
適應了好一會兒,發現窗戶前站了個人影,嚇了一跳,仔細辨別,才發現有些眼。
半側著子坐起來,的黑發鋪陳在肩上,襯得小臉越發白皙。
常燈下意識喊了一聲:“聞柏崇?”
那道影轉過來,往這邊走了兩步,右手的繃帶一角散開,順著手臂垂下,寂靜深夜里,男人神冷的像冰,雙眸平靜,直到走到床邊,才堪堪停住腳。
“嗯?”
常燈仰著臉:“你不睡覺站那干嘛?”
大半夜他像鬼一樣站在窗前,迎著風也不知道在想什麼,一靠近就察覺到他上的涼意。
說完,視線下落,昏暗的線下,紗布上暈染一片深。
常燈瞬間清醒了,下床開大燈。
果然,聞柏崇的右手又滲出了,將紗布都染。
關鍵本人還一臉淡定,似乎不覺得疼。
Advertisement
常燈麻利地翻出從醫院提回來的一兜子藥品,找到紗布和止棉,向他招手:“過來。”
“別折騰了,睡你的去。”男人并不順從,還直愣愣地站在那。
“很快的,重新上個藥,包一下就行。”常燈不管他說什麼,徑直走過去,“你不過來的話那我只好到這邊來了,手出來。”
語氣自然,孩滿眼都是怎麼上藥和包扎,毫沒注意到男人眼底一閃而過的晦暗。
幸好不太嚴重,理完不過十分鐘。
“怎麼又裂開了?”常燈將東西都規整好,“你也不知道重新弄一下?”
“死不了。”
“到底怎麼弄得,你睡覺著這只手了?”
“不是。”男人惜字如金。
“那是怎麼回事……”常燈眼尖,一把抓他的左手,指尖上還沾著跡,蹙眉,質疑,“你自己抓的?”
聞柏崇眸子漸漸回暖,沒吭聲。
常燈明白了。
許是見著男人神竟有些頹廢,他的眉眼寡淡,像被水泡過一般,莫名沖淡了平時那凌冽,顯得有些無神,放輕了語氣:“是不舒服嗎?。”
“嗯。”
常燈看了眼沙發,正常人睡著都不舒服,更何況病號,從床上撈起自己的小毯子:“咱倆換換吧,我個子低一些,睡沙發正好,你睡床。”
“你睡你的。”
男人說罷,也不管的表,又要往沙發上躺。
修長的軀蜷在沙發里,姿勢怎麼看怎麼別扭,倒是怪可憐的。
Advertisement
“我們換一下吧,你睡沙發不舒服。”
“嘖,你睡你的,別管我。”他回。
常燈糾結半天,嘆了口氣,蹲在沙發邊,試探著問:“那——要不,你也上床來睡吧?”
已經答應試著像正常夫妻那樣相了,是該邁出第一步。
“你說的。”
聞柏崇作比快,撈起沙發上的枕頭就從另一邊上了床,作迅速地像是有狗在攆他,沒等常燈反應過來,已經舒服地躺上床了。
常燈:“……”
好像落圈套了呢。
“骨頭你不會反悔吧?”男人角勾著笑,神傲然,“不許反悔,反悔也沒用。”
五分鐘后,大燈熄滅。
房間里只剩下床頭燈的昏暗余。
常燈平躺著,心臟跳的很快。
這還是第一次和一個異躺在同一張床上,手可及的位置,說不張是假的。
只不過,聞柏崇好像也沒有那麼淡定,都能聽見他刻意制的呼吸聲,之前還能說,真的躺下之后,他反而不自在了,默默往床邊挪。
即使作很輕,常燈依舊能捕捉到。
笑了笑:“你張啊?”
“誰張了?”
“你別掉下床了。”
“你以為我像你一樣傻麼?”
“切。”常燈翻了個,背對他,“我睡了,別吵。”
后面窸窸窣窣一陣響,布料的聲音很輕,但在安靜的空間里卻無限放大,常燈怕他又去抓傷口,只好翻朝著他睡,將聞柏崇的右手捉住。
Advertisement
手下的軀一僵,也不敢,只能覺到脈搏跳的頻率。
男人口不饒人,冷嗤一聲:“你還真不客氣,這就上手了?”
話畢,他又說:“上手也不是不行吧……”
困意襲來,常燈思維漸漸混沌,只說了句:“別臭了,快睡。”
聞柏崇直愣愣地躺著,聽著邊孩平緩的呼吸聲,竟然莫名覺得舒適,手腕還被的手指圈住,從皮相接的地方蔓延出一陣難以言說的異樣。
他作放輕,微側著子,冷峻的眸子染上幾分和,在不甚明亮的環境中細細打量著枕邊的孩,很白,睫很長,尾端微微上翹,纖細濃,鼻尖盈滿淡淡的梔子花香,夾雜著一藥苦味。
和這個人一樣,看似實則堅韌。
他出左手了下常燈的耳垂,圓潤的充斥著指腹,哼笑一聲:“傻不拉嘰的病秧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286 章

我成了反派的親閨女
反派陸君寒,陰險狡詐,壞事做盡,海城之中,無人不怕。可最後卻慘死在了男主的手中,成了海城圈子裡的大笑話!錦鯉族小公主為了改變這一悲慘結局,千方百計的投胎,成了陸君寒的親閨女陸梨。三歲半的小糰子握緊拳頭:爸爸的生命就由我來守護了!誰都不能欺負他!眾人臉都綠了,這到底是誰欺負誰?!後來——陸君寒:「來人!把他扒光扔到池子裡。」陸梨:「爸爸,我來吧!脫衣服這事我會的。」「……」陸君寒頓了頓:「算了,脫衣服礙眼,把他一隻手給我砍——」話未說完,陸梨先亮出了刀:「我來我來!爸爸,這個我也會的!」陸君寒:「……」事後,有記者問:「陸總,請問是什麼讓你洗心革麵,發誓做個好人呢?」陸君寒含笑不語。為了不帶壞小孩子,他不得不將所有的暴戾陰狠收起,豎立一個好榜樣,將小糰子掰回正道,還要時時刻刻防著其他人騙走她!……可誰知,小心翼翼,千防萬防養大的寶貝閨女,最後居然被一個小魔王叼了去!向來無法無天、陰險狠戾的小魔王一臉乖巧:「梨梨,他們都說你喜歡好人,你看我現在像嗎?」【團寵!巨甜!】
191.4萬字8 30842 -
連載2746 章

暖心甜妻,凌總晚安
蘇熙和淩久澤結婚三年,從未謀麵,極少人知。晚上,蘇熙是總裁夫人,躺在淩久澤的彆墅裡,擼著淩久澤的狗,躺著他親手設計訂製的沙發。而到了白天,她是他請的家教,拿著他的工資,要看他的臉色,被他奴役。然而他可以給她臉色,其他人卻不行,有人辱她,他為她撐腰,有人欺她,他連消帶打,直接將對方團滅。漸漸所有人都發現淩久澤對蘇熙不一樣,像是長輩對晚輩的關愛,似乎又不同,因為那麼甜,那麼的寵,他本是已經上岸的惡霸,為了她又再次殺伐果斷,狠辣無情!也有人發現了蘇熙的不同,比如本來家境普通的她竟然戴了價值幾千萬的奢侈珠寶,有人檸檬,“她金主爸爸有錢唄!”蘇熙不屑回眸,“不好意思,這是老孃自己創的品牌!” 蘇熙淩久澤
238.3萬字8.18 580395 -
完結565 章
帝少豪寵小嬌妻
一張不孕癥的檢查單將蘇心棠直接送入婚姻的墳墓, 疼愛的表妹成了小三,懷著身孕登堂入室 婆婆步步緊逼,蘇心棠的婚姻變成一地雞毛...... 不知何時,一個神秘而權勢通天的人出現在她身后, 他的聲音冷淡魅惑:“跟著我,我帶你登上頂峰。”
89.9萬字8 185066 -
完結4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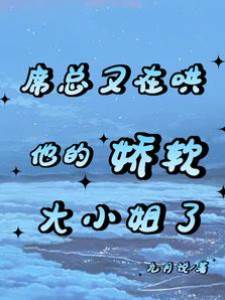
席總又在哄他的嬌軟大小姐了
矜貴腹黑高門總裁×嬌俏毒舌大小姐【甜寵 雙潔 互撩 雙向奔赴 都長嘴】溫舒出生時就是溫家的大小姐,眾人皆知她從小嬌寵著長大,且人如其名,溫柔舒雅,脾氣好的不得了。隻有席凜知道,她毒舌愛記仇,吵架時還愛動手,跟名字簡直是兩個極端。席凜從出生就被當成接班人培養,從小性子冷冽,生人勿近,長大後更是手段狠厲,眾人皆以為人如其名,凜然不已,難以接近。隻有溫舒知道,他私下裏哪裏生人勿近,哄人時溫柔又磨人,還經常不講武德偷偷用美人計。兩人傳出聯姻消息時,眾人覺得一硬一柔還挺般配。溫舒第一次聽時,隻想說大家都被迷了眼,哪裏般配。經年之後隻想感歎一句,確實般配。初遇時,兩人連正臉都沒看見,卻都已經記住對方。再見時兩人便已換了身份,成了未婚夫妻。“席太太,很高興遇見你。”“席先生,我也是。”是初遇時的悸動,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心動。
89.3萬字8.18 19853 -
完結1891 章

第一寵婚:秦少心頭寶
深城皆傳她‘招秦又慕楚’,她冤,其實是前有狼后有虎。深城又傳她‘拆東為補西’,她冤,其實是人善被人欺。楚晉行冷臉:“我女朋友。”江東皮笑肉不笑:“我妹。”秦佔點
332.8萬字8.18 88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