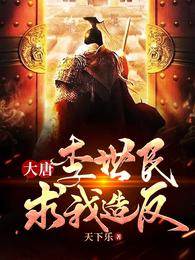《天唐錦繡》 第二千零七十九章 國家制度
;
第5145章 國家制度
大唐與大食分立東西,皆當世強國,但兩國在本質上卻完全不同。
大唐之強盛在於制度,完善的制度使得帝國良好運轉,無需明君、無需良將,只要其國沒有、沒有掣肘,這架完的國家機自我運轉之下,便足以抵任何外來侵略。
但這也正是大唐的弱點。
何謂「制度」?
簡而言之,便是「規則」。
一切都要在規則之下運行。
大唐可以勞師遠征,但不能持久,因為大量消耗糧秣、兵力,就損害了國家利益,君王存在的最大意義便是維護國家利益,一旦與此相悖,君王的權力便要遭限制,甚至顛覆。
連續在西域、河中展開大戰,甚至將西域戰區長久繼續下去,必然得到大唐國強烈反對,來自於部的掣肘足以使得安西軍的戰略難以為繼,即便是房俊也無法服各路反對聲音。;
「規則」是一柄雙刃劍,得益於規則,就要制於規則。
一旦破壞規則,其反噬足以天翻地覆……
而大食則完全不同。
與其稱其為「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個「部落聯盟」,哈里發命於「真神」、獲取最強大的世俗權力,以強橫之武力展開徵伐,推行信仰的同時,通過戰爭攫取財富、資,征服異族而不斷壯大。
可以說,整個大食的運行皆在於哈里發的強權,以戰爭的模式維繫國家運轉。
通過破壞、摧毀、殺戮、掠奪來發展壯大。
他們從不建設,只會破壞。
只要哈里發願意,某種程度上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征伐各族組聯軍,對大唐進行無休止的戰爭。
Advertisement
當今次大食戰敗、明日捲土重來,安西軍還能籌集足夠的糧秣輜重,再打一次「西域之戰」嗎?;
皇帝、大臣、世家、門閥……會允許一支數萬人的部隊長期駐紮於西域,不斷消耗糧秣輜重嗎?
……
房俊微微頷首:「大論見解深刻、鞭辟裡,大唐的確不可能長期在西域保持戰爭狀態,這是掣肘,但也正因如此,才彰顯出大唐制度之優越。」
祿東贊不得不予以認同。
天下沒有最好的制度,國家也好、部族也罷,最重要是因地制宜、取長補短,「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別國的好制度,照搬過來未必適用於自己。
但所有的好制度必然有一個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共同點,那就是君權必須得到限制。
大食也好、拜占庭也罷,他們的君權的確得到限制,但高高在上的「神權」卻恣無忌憚。
而這一點,大唐做的最好。;
他深了解過大唐的制度,無論是軍機、亦或是政事堂,將軍政分開,既相互對立、制約,又彼此協同、互補,輕易不會出現文指揮戰爭、武將淪為傀儡,或者武將掌握大權、隨意干涉政務那等混況。
軍政雙方、各司其職,皇帝更像是一個大管家,提綱契領、平衡各方,而不是「王權霸道」「言出法隨」。
再優秀的個人也會犯錯,而一個專業的團隊所做出的決定,必然照顧了儘可能多的利益,肯定比個人決斷更加合理、也更加穩健。
但是大唐的這一套制度,無論大食、亦或吐蕃,想學也學不來。
若是照搬過來,頃刻間便摧毀了原本賴以立國的權力構架,陷混、無序,分崩離析只在旦夕之間……
Advertisement
房俊端坐,目湛然:「帝國當然不可能支撐起在西域發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但是對於安西軍來說,這一戰也用不到曠日持久。」;
祿東贊不解:「即便大唐此戰獲勝,但也僅只是擊潰大食軍隊而已,想要全殲絕無可能。不能予以全殲,這些潰兵逃回大馬士革,很快又會被整編、組織,不久之後還會繼續攻伐西域……二郎如何應對?」
房俊笑道:「這是戰略機,暫時無可奉告,不過大論既然在軍中,用不了多久便會親眼目睹。」
祿東贊搖搖頭,對房俊裝神弄鬼無可奈何,但他依舊心存懷疑。
二十萬大軍想要擊敗不難,但想要徹底將其摧毀、使其不能捲土重來,卻是難如登天。
上一次「西域之戰」唐軍大獲全勝,甚至差一點將穆阿維葉留在這裡,可這才幾年時間大食便再度組織軍隊、興兵來犯?
裴行儉這時問道:「是否依照計劃行事?」
房俊頷首,道:「傳令薛仁貴,無需在意恆羅斯城,其部前出追著敵軍潰兵至可散城,要給予敵人迫,使其自陣腳。另外,咱們一起去看看那位大食將軍阿米爾,據聞此人去年率領麾下軍隊將波斯殘餘全部殲滅,使得波斯全境納大食之版圖,卻不知是何等人傑?」;
裴行儉笑道:「被扎了兩刀便忙不迭自份、哀求投降,算得什麼人傑?」
房俊看了祿東贊一眼,意味深長:「當然算得上人傑,畢竟,『識時務者為俊傑』。」
裴行儉大笑。
祿東贊也忍不住笑:「二郎這是敲打老夫呢?」
房俊道:「心照不宣即可,何必說出來呢?看不說,還能做朋友!」
Advertisement
祿東贊:「……」
*****
可散城陷恐慌。
雖然都懂得天下無必勝之戰的道理,也都知道阿米爾此戰更多還是對於唐軍的試探,可敗得如此之快、如此之慘,卻實在出乎所有人的預料,不可接。
葉齊德坐在營帳之大發雷霆:「阿米爾誤我!我幾次三番強調唐軍之強大,要求各部穩紮穩打、不可貪功冒進,結果誰聽我的?都以為碎葉城是一枚碩大的軍功章,任誰上去都能手到擒來!結果信心百倍的去了,卻被人打的大敗虧輸、全軍覆滅!」;
前次「西域之戰」慘敗的影瞬間籠罩心頭,無可遏止的恐懼蔓延開來。
馬斯拉瑪有些不滿,戰略是大家一起制定的,無論此前存在何等分歧,最起碼在阿米爾率軍攻打碎葉城的這一步是所有人的共識,豈能戰場遇挫便推卸責任?
「大帥,阿米爾雖敗,但討回來的兵卒不在數,並非全軍覆滅。」
葉齊德氣呼呼道:「那又差了多?數萬兵馬,陷在恆羅斯城中的超過大半,回來的連三分之一都沒有,你卻跟我摳字眼?」
馬斯拉瑪心平氣和:「非是在下與大帥摳字眼,只是回去大馬士革的戰報務必準,更要實事求是。」
大家一起輔佐葉齊德攻伐西域,某種意義上是哈里發委派他們幾人扶葉齊德一程,更是認可他們將來為葉齊德的班底,獲取一份「從龍之功」,所以立場一致、利益一致。;
可若是葉齊德為了推卸責任而將所有過錯全部推到阿米爾頭上,可以想見未來阿米爾在大馬士革的境。
難免有亡齒寒之。
畢竟阿米爾此番大敗其實算不上是戰略失誤、更非畏敵怯戰,誰能想到唐軍將整個恆羅斯城的地下全部埋設火藥?
Advertisement
換了誰來都難免一個慘敗的下場。
葉齊德忍了忍,也知道此刻最重要是穩定軍心而非追究誰的責任,但對於阿米爾此前之不敬依舊念念不忘:「可現在阿米爾人呢?需要他集結潰兵、重整旗鼓的時候,他人去了哪兒?該不會是被唐軍給俘虜了吧?」
馬斯拉瑪與奧夫面凝重。
有兵卒快步前來,遞上一份戰報,稟報導:「據恆羅斯城潰軍所言,阿米爾將軍極有可能已經被唐軍俘獲!」
葉齊德一把接過戰報,仔仔細細看了一遍,怒哼一聲,將戰報丟在桌上:「無能之輩,愚蠢至極!你們剛才還維護他,現在他了俘虜,看看你們還要如何維護!」;
兩人先後看完戰報,唉聲嘆氣。
戰敗與被俘,這是完全不同的責任,單只是戰敗,或許還能依靠哈里發的重新重整旗鼓、東山再起,可一旦淪為俘虜,阿米爾的聲、功績馬上煙消雲散,再想獲取哈里發的信任,幾乎不可能。
唯一的指便是其族人能夠花費重金,從唐人手中將阿米爾贖回來……
奧夫道:「若阿米爾當真被俘,大帥應當主聯絡唐軍,先確保阿米爾的安全,然後與其洽談,花費重金將其贖回。」
葉齊德大怒:「敗軍之將,我不追究他的責任已經是寬宏大量,焉能花費重金去贖他?」
奧夫語重心長、苦口婆心:「阿米爾如今陷落敵營、淪為俘虜,往昔功績與聲一落千丈,最是驚惶恐懼之時,大帥若能出援手,其必然激涕零、銘記大恩。另外,若大帥能對一個敗軍之將展現仁、寬厚之心,其餘人同,必然使得大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馬斯拉瑪也道:「唐人有句諺語,做『千金買馬骨』,想來也是這個意思。」
葉齊德糾結半晌,心中不願,卻也不得不承認兩人的諫言有道理,只得著鼻子認下:「那就稍後派人聯絡唐軍,看看能否將阿米爾贖回來……可現在當務之急,是如何收拾殘局?」
猜你喜歡
-
完結143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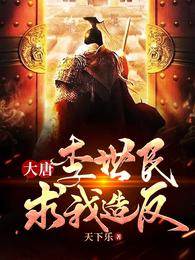
大唐:李世民求我造反
穿越大唐貞觀年的李恪,本想憑著自己傳銷講師的能力,洗腦一幫忠實班底,茍著當個不起眼的小王爺。 誰知道穿越八年後,卻發現自己還帶來了一整個國家戰略儲備倉庫。 於是李恪徹底放飛了自我,要當就得當個天不怕地不怕的逍遙王爺! 先整個報紙,刷刷名聲。 再整個煉鐵廠,掌控大唐鋼鐵煉製,從世家手裏搶搶錢。 接著為天下工匠和府兵謀個福利,團結一切可團結之人。 當長孫老陰人想要針對李恪的時候,卻發現,除了朝堂之上,外麵已經都是李恪了。 等李恪搞定一切,可以徹底逍遙的時候。 李世民:“恪兒啊,朕已經封你當太子了。” 李恪:“……”別啊,那個皇帝,狗都不當。
271萬字8 92915 -
完結663 章
少年無雙
天漢八年,冬至時分,北風朔朔,北奴王親帥大軍十萬,攻破雁門關。燕州塗炭,狼煙四起,屍橫遍野,十室九空,骸骨遍地!王命數十道,無一藩王奉昭勤王。龍漢岌岌可危!京師城外,紅衣勝火,白馬金戈。少年立馬燕水河畔,麒麟細甲,精鋼鐵面。長柄金戈,直指長空,目光如炬,視死如歸!一戈破甲八千,五千紅甲盡出行,七萬北奴留屍關中。見龍卸甲,少年歸來。從此龍漢少了一位神勇天將軍,多了一位少年書聖人。
92.6萬字8 90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