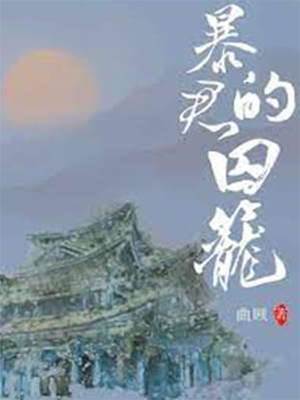《花嬌》 第82章 計謀
裴宴剛開始看那航海輿圖的時候還帶著幾分因為見過很多海圖的漫不經心,可越看,他的神越嚴肅。
難道這輿圖有什麼不妥?
雖說鬱棠對自己的推斷有信心,可面對的是裴宴,年紀輕輕就中了進士,曾經在京城六部觀過政,見多識廣的裴宴,心裡不免有些懷疑起自己來。
裴宴則在暗中倒吸了一口涼氣。
他又重新將那輿圖仔細地察看了一遍。
鬱棠到底沒能忍住,有些戰戰兢兢地道:“三老爺,這輿圖……”
裴宴把手中的凹凸鏡丟在了這幅臨摹的輿圖上,皺了皺眉,面凝重地走到了書案旁的小圓桌邊,指了指圓桌旁的圈椅,道:“我們坐下來說話。”
鬱文和鬱棠不由換了一個不知所措的目,然後小心翼翼地坐了下來。
裴宴親自給父倆各續了杯茶,這才沉聲對二人道:“你們能不能把怎麼發現這幅輿圖的詳細經過再重新給我講一遍。”
鬱文看著裴宴肅穆的表,知道這件事很有可能非常重要,不敢添油加醋,又怕自己說得不清楚影響了裴宴的判斷,指了鬱棠道:“這件事是你發現的,還是你來給三老爺好好說說。”
鬱棠組織了一下語言,把事的經過詳細地講了一遍。
期間裴宴一直很認真地聽著。
父倆的說辭大同小異,可見鬱家能發現這件事純屬意外。
也就是說,李家是知道這幅畫有問題的。
這其中還牽扯到福安彭家。
裴宴等到鬱棠說完,想了想,道:“我原以為這只是一幅普通的輿圖。你們家既然不想卷這場紛爭,就想了個能幫你們家困的主意——把這幅輿圖拿出來,裴家做委托人,幫你們拍賣了,價高者得。你們家既可以得些銀子,又可以名正言順地擺這件事。這也算是鬱老爺做了好事的報酬。”
Advertisement
鬱棠聽著覺得眼前一亮。
裴三老爺的這個主意可真是太好了!
與其遮遮掩掩地讓人懷疑他們家已經知道輿圖的容,不如公開拍賣,讓那些有能力、有勢力、還能自保的人家得了去,你們有本事去找人家的麻煩啊,別欺負他們鬱家。
他們鬱家只不過是個平凡普通的商戶而已。
可聽裴宴這語氣,現在好像又不能這麼做了。
鬱棠心裡著急,忍不住打斷了裴宴的話,急切地道:“那現在又為什麼不行了呢?三老爺您可真是厲害,轉眼間就想出了這樣的好主意。”
這馬屁拍得心甘願。
如果裴家願意做這個中間人出面幫他們家拍賣這幅輿圖,他們就能徹底地從中摘出來了。而且,有能力拍到這幅輿圖的人,不可能是無名無姓的家族,就算不能像福安彭家那樣顯赫,恐怕也不是那麼好惹的。
到時候李家就好看了。
辛辛苦苦花了那麼多力弄來的輿圖不是獨一份了,那他們在彭家面前又有什麼還能拿得出手呢?
熱切地著裴宴。
鬱文也熱切地著裴宴,道:“是這幅輿圖有什麼問題嗎?這圖雖然是請人臨摹的,但臨摹的人手藝很好,還悄悄加蓋了私章的。”
萬一有什麼不妥,不知道找錢師傅還有沒有用?
裴宴這才驚覺自己無意間賣了個關子。他笑道:“倒不是這輿圖有什麼問題,而是這輿圖太珍貴了。是拍賣,還是以此哪家的商鋪,還得你們自己拿個主意。”
這笑容,也太燦爛了些吧?
那一瞬間,仿佛冰雪消融,大地回春,整個面孔仿佛都在發,英俊地讓人不能直視。
鬱棠看著裴宴的臉,半晌才回過神來。
Advertisement
這次他也應該是真笑。
自己何其幸運,居然一天看到裴宴兩次真心的笑容。
鬱棠在心裡嘖嘖稱奇,不敢多想,朝父親去。
只見父親神呆滯,好像被這消息砸中了腦袋似的。
忙喊了一聲“阿爹”。
鬱文一個激靈,腦子開始重新轉了起來。
他們鬱家家底單薄,這輿圖太珍貴了,拿在他們手裡,就如同三歲的小孩舞大刀,本舉不,不是把別人割傷,就是把自己給割傷。從現在的形勢看,他們會被割傷的機率遠比割傷別人的機率大得多。
鬱文立馬就有了決斷。他道:“三老爺,這是幅什麼輿圖?怎麼會像您說的那麼貴重?我們要是想像您所說,依舊請了裴家做中間人,能把這輿圖給拍賣了嗎?”
裴宴頗為意外,目卻是落在了鬱棠上。
他知道,鬱家的這位大小姐是很有主見的,鬱文未必能管得住。
鬱棠是讚父親的決定的。
有多大的碗,就吃多的飯。
吃著碗裡的,還看著鍋裡的人,通常都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
雖然也好奇這輿圖是如何地珍貴,但怎樣能把鬱家從這場龍卷風似的事件裡摘出來,全家平安無事才是最重要的。
鬱棠連忙朝著裴宴點了點頭,表達了自己的意見。
裴宴自嘲地笑了笑。
他突然知道自己為何願意幫鬱家了。
不是鬱小姐長得漂亮,也不是鬱文為人豁達,而是鬱家的人一直都看得很通。
哪怕是富貴滔天,可也要能承得住才行。
他見過太多的人,在權勢的浮雲中迷失了方向。
包括年輕時的他自己。
這才是鬱家最難能可貴的。
特別是鬱小姐——鬱文有這樣的心,與他的年紀和閱歷有關,從他不再去考舉人就可以看出來,並不稀奇。但年紀輕輕的鬱小姐也有這樣的襟和氣度,就令人刮目相看了。
Advertisement
他深深地看了鬱棠一眼,決定在這件事上再幫鬱家一次。
“雖然同是海上生意,你們可知道海上生意也是分好幾種的?”裴宴收起戲謔之心,鄭重地道,“當朝市舶司有三,一是寧波,一是泉州,一是廣州。而海上行船的路線,不是去蘇祿的,就是去暹羅或是去錫蘭的,可你們這張輿圖,卻是去大食的。”
鬱文和鬱棠聽得腦子暈呼呼的,面面相覷。
蘇祿是哪裡?錫蘭又是哪裡?大食很重要嗎?
鬱棠不想父親在裴宴面前沒面子,搶在父親說話之前先道:“三老爺,您這話是什麼意思?是去大食的船很嗎?所以這幅輿圖很值錢?”
“不是!”裴宴看出父倆都不懂這些,細心地解釋道,“我朝現有的船隊,不管是去蘇祿也好,去暹羅也好,最終都希這些東西能賣去的是大食。因為大食是個非常富庶的王國。從前我們誰都不知道怎麼直接去大食,所以只能把貨販到蘇祿、暹羅等地,再由他們的商賈把東西販到大食去。你們這幅輿圖,是條新航線,是條我們從前想去而一直沒能去的航線。而且這條航線是從廣州那邊走的,就更顯珍貴了。”
鬱文父還是沒有聽懂。
裴宴就告訴他們:“朝廷因為倭寇之事,幾次想閉關鎖海。特別是寧波和泉州的市舶司,各自都已經被關過一次了。最近又有朝臣提出來要裁撤這兩的市舶司。若是廷議通過,這兩的市舶司有可能會被再次裁撤。船隊就只能都從廣州那邊走了。你說,你們這幅輿圖珍不珍貴?”
鬱文和鬱棠都瞪大了眼睛。
也就是說,他們家就更危險了。
父倆不由異口同聲地道:“拍賣!裴三老爺,這輿圖就拍賣好了。”
Advertisement
鬱文甚至覺得拍賣都不保險,改口道:“裴三老爺,您想不想做海上生意?要不,我把這輿圖送給您吧?我們不要錢。就當是報答您幫拙荊找大夫的謝禮了。”
裴宴臉發黑。
他做好事,居然還做了巧取豪奪!
鬱棠覺得他爹這話說得太直白了,像是甩鍋似的,再一看裴宴,臉黑黑的,的腦子前所未有地飛快地轉了起來,話也飛快地說出來:“阿爹,您這就不對了。裴三老爺要是想要這幅輿圖,直接跟我們易就是了,怎麼會又說替我們家做保,拍賣這幅輿圖呢?”
“是啊,是啊!”鬱文這才察覺自己說錯了話,朝著裴宴訕笑。
鬱棠則怕裴宴一甩手不管了。
只有裴家這樣的人家,才有可能邀請到和彭家勢力相當的世家大族來參加拍賣,才能保證他們家的安全。
好話像白送似的不住地往外蹦:“三老爺可不是這樣的人!您不知道,我從前去裴家當鋪的時候就遇到過三老爺……”劈裡啪啦地把兩人的幾次偶遇都告訴了鬱文。
鬱文汗, 給裴宴道歉:“都是我說話沒過腦子……”
裴宴看著鬱棠那紅潤的小一張一合地,覺邊好像有幾百隻麻雀在嘰嘰喳喳地似的,腦殼都有些地疼。
他打斷了鬱棠:“行了,行了,從前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鬱棠就不提從前的事,繼續捧著裴宴:“可我覺得您說的真的很有道理。最好的辦法就是拍賣了。不過,既然這副輿圖這樣珍貴,您說,我們能不能請人多臨摹幾份,然後把它們都拍賣出去。我從小就聽我大堂伯說,做生意最忌諱吃獨食了。你吃獨食,大夥兒眼紅,就會合起夥兒來對付你。要是多幾家一起做生意,他們總不能每家都嫉妒吧?”
裴宴簡直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小丫頭,還跟他玩起心眼來。
怕鬱家不能置事外就直說,拐這麼大個彎,不就是想他們裴家,他裴宴出面背這個鍋嗎?
( = )
猜你喜歡
-
完結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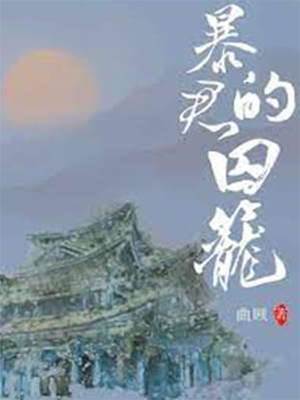
暴君的囚籠
鎮國公家的幼女江知宜自幼體弱,一朝病重,眼看就要香消玉殞。有云遊的和尚登門拜訪,斷言其命格虛弱,若能嫁得像上將軍那樣殺氣重、陽氣足的夫婿,或許還能保住性命。鎮國公為救愛女、四處奔波,終於與將軍府交換喜帖,好事將成。然而變故突生。當夜,算命的和尚被拔舌懸於樑上,上將軍突然被派往塞外,而氣咽聲絲的江知宜,則由一頂轎攆抬進了皇宮。她被困於榻上一角,陰鷙狠絕的帝王俯身而下,伸手握住她的後頸,逼她伏在自己肩頭,貼耳相問,“試問這天下,還有比朕殺氣重、陽氣足的人?”#他有一座雕樑畫棟的宮殿,裡面住著位玉軟花柔的美人,他打算將殿門永遠緊鎖,直到她心甘情願為他彎頸# 【高亮】 1.架空、雙潔、HE 2.皇帝強取豪奪,愛是真的,狗也是真的,瘋批一個,介意慎入! 3.非純甜文,大致過程是虐女主(身)→帶玻璃渣的糖→虐男主(身+心)→真正的甜
27.4萬字8 29018 -
完結2913 章
妃本良善:皇上請下堂
他是西玄冷漠狠戾的王,卻因一名女子,一夜癲狂,華發如霜。她,便是大臣口中被他專寵的佞侍。“除了朕,誰都不能碰她!” 案一宮宴,某女給了挑釁妃子一記耳光“勾心鬥角太累,本宮喜歡簡單粗暴。” 某帝“手疼不疼?” 某女斜睨某妃“這就是我跟你的差別,懂?” 案二某帝鳳眸輕抬“把朕推給其他嬪妃,朕在你心裏就那麼不值錢?” 某女聳肩“不就是個男人?我若想要,滿大街的男人任我挑。” 轉身某女便被吃幹抹淨,某帝饜足哼笑,“挑?”
262萬字8.18 49515 -
完結300 章
和親太子妃的千層馬甲
北燕太子迎娶盛涼公主前夕,小乞丐阿照被送上和親馬車,成了嫁妝最多的代嫁公主。面對太子的厭惡找茬,阿照不悲不喜,從容面對。然而,當昔日故人一個個對面相見不相識時,陰謀、詭計、陷害接踵而來,阿照是否還能從容應對?當隱藏的身份被一層層揭開,那些被隱藏的真相是否漸漸浮出了水面? ――##1V1##―― 她是喜歡周游列國游山玩水的天真少女,也是循規蹈矩秀外慧中的大家閨秀。 她是和親異國的代嫁太子妃,也是那陰狠公子豢養在身邊的丑奴。 她是街角蓬頭垢面討飯的小乞丐,也是他國攝政王贈予金令的干閨女…… ―...
54.2萬字8 7262 -
完結154 章

冷美人撩完就跑,瘋批王爺哭著找
【清冷釣係舞姬(有隱藏身份)X不近女色瘋批王爺】【類似追妻 強製愛 男外強內戀愛腦 複仇 雙潔HE】不近女色的王爺蕭以墨,竟從別人手中奪了清冷金絲雀可江念綺與其他貴子的美人不一樣,不爭不搶不求名分蕭以墨擒住她下巴:“念綺,你難道不想當王妃?”“我自是有自知之明,不會奢求那些。”江念綺清冷的眉眼淺然一笑,這一笑卻讓他愈發瘋狂世人說她是個聰明人,乖乖跟著王爺就有享不盡的榮華她肯定離不開王爺,就連蕭以墨自己也這麼認為但當蕭以墨替她奪了這天下,想要納她入宮時江念綺卻連夜逃走了,悄無聲息。“她肯定以為朕要娶世族貴女為後,跟朕鬧脾氣了。”正在高興她吃醋時,探子來報,她當初竟是有預謀接近,故意利用他的權勢複仇。蕭以墨胸口瞬間疼的心慌意亂:“朕寵著她,哄著她,可她竟在朕眼皮底下跑了。”再見時,那孤傲又不可一世的蕭以墨把她摁在懷裏。嘶啞低哄:“念綺,跟朕回去,好不好?”【偏女主控,瘋批霸道強製愛,類似追妻火葬場,重甜輕虐】
28.2萬字8 19107 -
完結124 章

吾妻甚是迷人
【嬌軟妖精X清冷太子,雙潔/重生/超甜!超撩!兄長超強助攻!】天凰國嫡出四公主溫若初,傳聞容貌驚人,如仙如魅,琴棋書畫無一不精通。是世間難得的嬌軟美人。眾人不知的是,自小兄長便在她房中掛起一副畫像,告訴她畫中之人是她夫君。一朝被害失去大部分記憶,她終於見到了畫中的夫君,比畫中來得更為清俊矜貴,身為顏控的她自然眼巴巴地跟了上去。“夫君,抱我~”“......”元啟國太子殿下,生性涼薄,宛如高懸明月。自及冠那年,一直困擾在一段夢鏡中,夢中之人在他求娶之時,轉嫁他人。尋人三年,了無音訊。正當放棄之時,在一處淺灘上遇到那女子,她嬌軟地撲向他,叫他夫君。劇場一花采節在即,京城各家貴女鉚足了勁兒爭奪太子妃之位。豈料霽月清風的太子殿下,親自從民間帶回了一名女子養在府中,各方多加打探均未知曉此女子的身份。眾人皆笑太子殿下竟為美色自甘墮落,高嶺之花跌落神壇;未曾想太子大婚當日,天凰國新任國君奉上萬裏紅裝,數不盡的金銀珠寶從天凰運送至元啟,並簽下了兩國百年通商免稅條約,驚得等看笑話的眾人閉了嘴,這哪是路邊的野薔薇,明明是四國中最尊貴的那朵嬌花!
22.9萬字8 14339 -
完結121 章

在遠古養大蛇
宋許意外成爲了一名遠古叢林裏的部落獸人,獸型是松鼠。 她所在的小部落被猛獸部落攻佔合併,宋許獨自逃進一片黑暗森林。 這片森林被一個蛇類半獸人所佔據,作爲一個曾經的爬寵愛好者,宋許看着漂亮蛇蛇狂喜。 宋許:好漂亮的尾巴!我完全可以!Boki!
20萬字8 14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