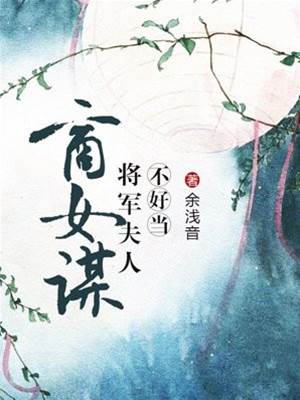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半城風月》 第42章 十全大補
暮時分,太山頂細細下了一場雨,半座青帝宮都陷在雲中,楠木迴廊上一片溼潤,瑪瑙棋子手微涼。
扶蒼緩緩將棋子放在棋盤上,對面的青帝便吸了口氣,苦笑:“這段時間你的棋路殺伐之心很重。”
扶蒼默然不答,一枚枚將瑪瑙棋子納盒中,方問:“還來麼?”
青帝搖頭嘆息:“不來了。這可不像你平時,還在氣我答應牽線燭氏的事?”
扶蒼倒了一杯九九歸元茶,推去他面前:“父親,我已說過暫時無心此事。”
“哦?”青帝目中帶了一笑意,“那就是劍道上又遇到難了?”
“不,倒是近期似有所悟,須得靜心一段時間來突破境界。”
“難道是心裡有另外喜歡的神?”
“……不是。”
“下雨心不好?”
扶蒼無奈地擡頭:“父親,輸了棋不必找這麼多借口。”
青帝吹了吹茶麪上的碧葉,悠然開口:“你自小就喜歡擺一張爹不疼娘不的冷臉,不知道的還當我嚴苛似鬼。上回遇到赤帝,他說我管教太嚴,弄得你寡言語,我竟不知何日才得洗清這番冤。”
扶蒼垂首微微一笑:“與言語無味者,自然惜字如金。”
“看來,言語無味者也太多了些。”青帝拭去棋盤上的溼痕,忽然想起什麼似的,又道:“說起燭氏,那位鐘山帝君果然手段了得,聽聞舒神拒絕替燭公主療傷,他竟扣了飛廉神君不放,每日送一把染的月砂去舒宮,把舒氣得不輕。”
Advertisement
說到此,青帝又有些失笑:“這燭氏一族,還真是邪氣霸道得很,依我看,倘若再扣留多一些時日,舒大約也不得不屈服,這小丫頭哪是燭氏的對手,可惜後來竟又把飛廉放了。”
扶蒼扭頭飲茶,一言不發。
青帝饒有趣味地打量他:“上回從花皇仙島回來,你還跟我抱怨了幾句,怎的如今我一提燭氏你便不說話?對了,我還沒見過燭氏那小公主,聽說容貌清豔,舉止高貴,可是真的?”
扶蒼勾出一個近乎譏諷的笑,舉止高貴?
他忽然將盒的瑪瑙棋子重新取出,一粒粒放在盒蓋上,淡道:“父親何必總提燭氏,不如再與我下三盤,三局兩勝,倘若我贏了,卻有一事要求父親。”
“三局兩勝?”
青帝愕然,他這個兒子從哪裡學會的這套?
扶蒼一直平淡而清雅地維持華胥氏的禮儀尊貴,幾乎對所有事都冷眼旁觀,從不陷任何糾葛,該見客,便客客氣氣地見客;該拜先生,便不假思索地去拜師,天帝牽線燭氏公主,他也並不推辭地去了。
他素來都只行順其自然之事,然而——三局兩勝?這帶著爭勝意味的賭局是怎麼回事?
青帝只覺趣味更濃,不由笑道:“你要求我何事?”
扶蒼從小就是自己的事自己拿主意,他幾乎不做干涉,他這個做父親的對他素來很放心,今日忽然提出有事求他,他反而好奇萬分。說起來,自拜了白澤帝君做先生後,扶蒼便有些說不出的變化,像是瓷有了一口活氣似的,也不知這是好還是壞。
Advertisement
扶蒼眸流轉,淺淺而笑,將一枚瑪瑙棋子輕輕放在棋盤上,緩緩道:“無論輸贏,父親與我下完棋,自然便知道了。”
緩緩拆下包裹住指甲的細白布,再將在指甲上的蔻丹棉一點點撕開,玄乙舉起手,放在眼前滿意地看了片刻。
五片指甲在下是一種近乎明的淡桃,比起曾經鮮紅的蔻丹,這更顯,大半年的工夫沒白花。
傷不能走路的日子如此無聊,唯有梳妝打扮能興致。
長袖一揮,霎時間滿屋子飄的都是服,從淡雅霜到濃麗絳紫,各種應有盡有,當日來明殿,是爲了替裝裳,便用了足足二十隻大箱子,可惜,總覺著還是了幾件。
玄乙爲難地挑選半天,勉強選了一件與指甲同的子,襬浸染了晚霞的茶花,配上流雲薄紗披帛,還算能看罷……唉,該做點新裳了。
對著梳妝鏡穿戴齊整,剛把點綴的金環進發髻,便聽仙在殿外喚:“玄乙公主,早膳來了。”
的臉頓時垮了下去,推開窗看看仙手裡的食盒,緩緩嘆了口氣:“……還是十全大補湯嗎?”
仙臉上怎麼看都帶著一子幸災樂禍的笑容:“不錯,這是古庭神君和芷兮神的一片心意,公主了傷不能走路,什麼時候傷好了,纔不用喝十全大補湯呢。”
哼,這個趾高氣昂的公主也終於有被折磨的一天!仙看著的苦瓜臉,覺得蠻開心的。
Advertisement
玄乙接過食盒,慢慢打開,毫無意外,裡面只有一碗濃稠的鮎魚藥草湯。
卻說因爲傷不能,在紫府裡睡了兩個月,以前天呆在紫府也沒覺得無聊,如今不知怎麼搞的,大概看熱鬧看上了癮,竟很是懷念明殿,待傷口不流了,便回來繼續聽課。
誰知噩夢也就這麼來了,回到明殿一個多月,古庭和芷兮也不知從哪裡找來的什麼上古偏方,採了一堆藥草,天天仙給用天河裡的鮎魚燉十全大補湯,據說因爲是被鮎魚妖的長鬚所傷,所以鮎魚湯最有效。
有沒有效是沒看出來,只有種這輩子都再也不想見到鮎魚的覺。
玄乙沉默了片刻,眼眶慢慢紅了。
“我想吃瑪瑙白玉糕,桃花百果糕。”淚盈盈地看著仙。
又哭了!他纔不上當!仙堅強地撐起膛:“那些茶點對公主的傷無甚益,還請公主忍耐。”
“那綠豆涼糕也可以。”十分勉強地換了一種。
“公主,你傷了……”
“黃金慄蓉糕也不錯。”
“公主……”
“你連百草薄荷糕也不能帶嗎?”泫然泣。
“好……吧。”仙起的膛毫無骨氣又了回去,灰溜溜地替去找糕點。
等他端了一碟子茶點氣吁吁跑回來的時候,碗裡的十全大補湯已經空空如也,姿綽約的燭氏公主安靜地坐在冰凳上欣賞自己的指甲。
Advertisement
“……公主,十全大補湯你喝完了?”仙十分懷疑地著。
玄乙小小咬了一口黃金慄蓉糕,笑得猶如春風撲面:“是啊,喝完了。”
“真的?”
“真的。”
他怎麼就那麼沒法相信呢!仙警惕地將整個庭院掃視一圈,肯定有什麼蛛馬跡留下,他纔不會相信這個壞壞的公主!
“咦?一大早就有茶點吃?”一個甜溫的聲音自殿門前傳來。
玄乙愉快地朝他招手:“夷師兄,你回來啦。”
回到明殿也有一個多月,而這位青氏的神君卻不知在什麼地方逍遙快活,竟不回來聽課,奇怪的是白澤帝君居然不管他。
“是啊,想我了沒?”夷慢悠悠走近,先挑了一粒茶點丟裡。
玄乙笑瞇瞇地倒一杯茶遞過去:“想。”
他笑了:“乖,不枉我一回來就先趕著來接你聽課。”
猜你喜歡
-
完結1098 章

帝凰女毒天下
前世助夫登基,卻被堂姐、夫君利用殆盡,剜心而死。 含恨重生,回到大婚之前。 出嫁中途被新郎拒婚、羞辱——不卑不亢! 大婚當日被前夫渣男登門求娶——熱嘲冷諷:走錯門! 保家人、鬥渣叔、坑前夫、虐堂姐! 今生夫婿換人做,誓將堂姐渣夫踐踩入泥。 購神駒,添頭美女是個比女人還美的男人。 說好了是人情投資,怎麼把自己當本錢,投入他榻上? *一支帝凰簽,一句高僧預言“帝凰現天下安”, 風雲起,亂世至。 他摟著她,吸著她指尖的血為己解毒治病,一臉得瑟: “阿蘅,他們尋錯帝凰女了?” “他們不找錯,怎會偏宜你?” 他抱得更緊,使出美男三十六計……
176.4萬字8.38 401415 -
完結490 章

嫡女為謀
作為現代特種兵的隊長,一次執行任務的意外,她一朝穿越成了被心愛之人設計的沐家嫡女沐纖離。初來乍到,居然是出現在被皇后率領眾人捉奸在床的現場。她還是當事人之一?!她豈能乖乖坐以待斃?大殿之上,她為證清白,無懼于太子的身份威嚴,與之雄辯,只為了揪出罪魁禍首果斷殺伐。“說我與人私會穢亂宮闈,不好意思,太子殿下你親眼瞧見了嗎?””“說我與你私定終身情書傳情?不好意思,本小姐不識字兒。”“說我心狠手辣不知羞恥,不好意思,本小姐只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斬草除根。從此她名噪一時,在府里,沒事還和姨娘庶妹斗一斗心機,日子倒也快活。卻不料,她這一切,都被腹黑的某人看在眼里,記在了心里……
108.5萬字8 94612 -
完結43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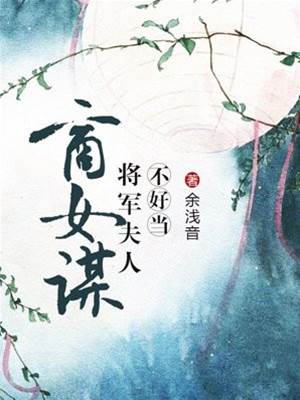
商女謀:將軍夫人不好當
一朝穿越,成為當朝皇商之女,好在爹娘不錯,只是那姨娘庶妹著實討厭,真當本姑娘軟柿子好拿捏?誰知突然皇上賜婚,還白撿了一個將軍夫君。本姑娘就想安安分分過日子不行嗎?高門內院都給我干凈點兒,別使些入不得眼的手段大家都挺累的。本想安穩度日,奈何世…
81.5萬字8 36634 -
連載287 章

世子嫌棄,嫡女重生後轉嫁攝政王
雲念一直以為自己是爹娘最寵愛的人,直到表妹住進了家裏,她看著爹爹對她稱讚有加,看著母親為她換了雲念最愛的海棠花,看著竹馬對她噓寒問暖,暗衛對她死心塌地,看著哥哥為了她鞭打自己,看著未婚夫對她述說愛意,她哭鬧著去爭去搶,換來的是責罵禁閉,還有被淩遲的絕望痛苦。 重來一世,她再也不要爭搶了,爹爹娘親,竹馬暗衛,未婚夫和哥哥,她統統不要了,表妹想要就拿去,她隻想好好活下去,再找到上一輩子給自己收屍的恩人,然後報答他, 隻是恩人為何用那樣炙熱的眼神看她,為何哄著她看河燈看煙火,還說喜歡她。為何前世傷害她的人們又悲傷地看著她,懇求她別離開,說後悔了求原諒,她才不要原諒,今生她隻要一個人。 衛青玨是人人懼怕的攝政王,從未有人敢正眼看他,可為何這個小女子看他的眼神如此不成體統,難道是喜歡他? 罷了,這嬌柔又難養的女子也隻有他能消受了,不如收到自己身邊,成全她的心願,可當他問雲念擇婿標準時,她竟然說自己的暗衛就很不錯, 衛青玨把雲念堵在牆角,眼底是深沉熾熱的占有欲,他看她兔子一樣微紅的眼睛,咬牙威脅:“你敢嫁別人試試,我看誰不知死活敢娶我的王後。”
52.8萬字8.18 5789 -
完結301 章

第三十年明月夜
第三十年,明月夜,山河錦繡,月滿蓮池。 永安公主李楹,溫柔善良,卻在十六歲時離奇溺斃於宮中荷花池,帝痛不欲生,細察之下,發現公主是被駙馬推下池溺死,帝大怒,盡誅駙馬九族,駙馬出身門閥世家,經此一事,世家元氣大傷,寒門開始出將入相,太昌新政由此展開。 帝崩之後,史書因太昌新政稱其爲中興聖主,李楹之母姜妃,也因李楹之故,從宮女,登上貴妃、皇后的位置,最終登基稱帝,與太昌帝並稱二聖,而二聖所得到的一切,都源於早夭的愛女李楹。 三十年後,太平盛世,繁花似錦,天下人一邊惋惜着早夭的公主,一邊慶幸着公主的早夭,但魂魄徘徊在人間的小公主,卻穿着被溺斃時的綠羅裙,面容是停留在十六歲時的嬌柔秀美,她找到了心狠手辣、聲名狼藉但百病纏身的察事廳少卿崔珣,道:“我想請你,幫我查一個案子。” 她說:“我想請你查一查,是誰S了我?” 人惡於鬼,既已成魔,何必成佛? - 察事廳少卿崔珣,是以色事人的佞幸,是羅織冤獄的酷吏,是貪生怕死的降將,所做之惡,罄竹難書,天下人恨不得啖其肉食其血,按照慣例,失勢之後,便會被綁縛刑場,被百姓分其血肉,屍骨無存。 但他於牢獄之間,遍體鱗傷之時,卻見到了初見時的綠羅裙。 他被刑求至昏昏沉沉,聲音嘶啞問她:“爲何不走?” 她只道:“有事未了。” “何事未了?” “爲君,改命。”
48.8萬字8 608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