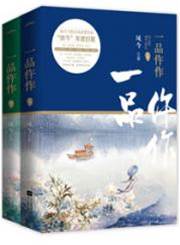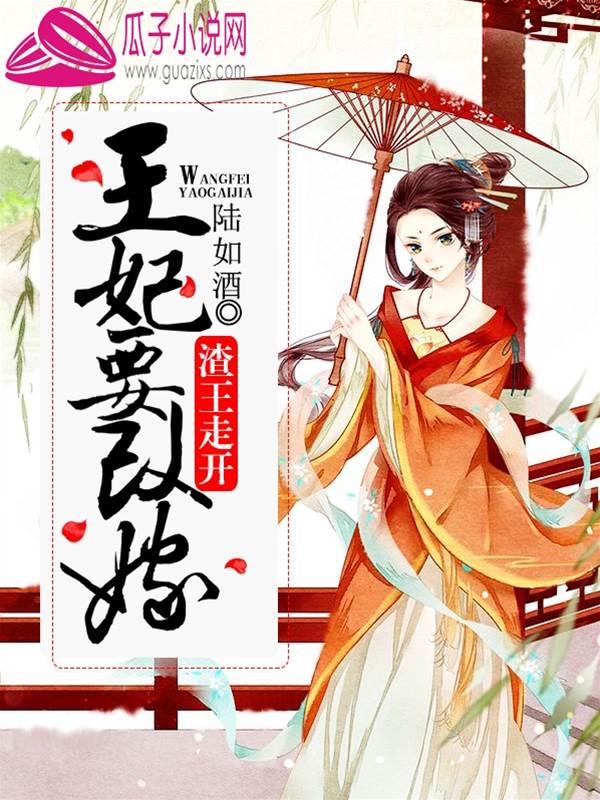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攻玉》 第97章 (1)
太子孝順慣了,再不好意思也只能恭謹聽著。
說來奇怪,有些人哪怕日日相見,也不見得會多加留意,杜庭蘭他才見三次,卻次次在心里留下了深濃的影子,如今聽著阿娘說到議親一事,那道窈窕的影,止不住在他心房里輕輕搖曳起來,這陌生的悸困擾著他,一方面讓他眉眼愈發溫,一方面又讓他無所適從,趁宮給阿娘送茶盞的當口,他轉臉沖藺承佑使了個眼。
藺承佑一本正經聆聽著皇后的教誨,面上比太子裝得還認真,似乎察覺了太子的眼風,他不神在案下用胳膊肘輕懟了太子一下,暗道:伯母最熱衷于給人說親,自從去年靜怡出降后,已經好久沒大展拳腳了,這才剛開始,且著吧。
好在宮人過來說倚霞軒的午膳已經備好,幾位大臣的夫人皆已席,就等著皇后駕臨了,劉冰玉才放兄弟倆一馬。
***
翌日,帝后及眾大臣啟程下山。
次日天剛亮,朝廷的旨意就頒布下來了。
香象書院最終定于二十五日開學,旨意上同時還公布了書院院長、、第一批學的八十名學生名單,除了那日同上驪山的那批,又添了不朝中員和外地節度使的千金。
當年的云書院院長一職是由盧國公夫人擔任,目下盧國公夫人年事已高難以再分神管理冗雜的書院事務,所以這回香象書院開學,院長只能另擬人選。
商議到最后,定下了兩位院長。
皇后人在宮中,遙領書院院長一職。
副院長則由國子監祭酒劉文昌的夫人擔任。
劉夫人為二品誥命夫人,早年也是長安有名的才子,年輕時錦心繡口,年長后更是德高重,消息一公布,朝野外眾口贊。
Advertisement
此外,書院里還設了司律、司德、司讀、司行四位,名單由皇后親自遴選,考察了好些時日,確保個個都德才兼備。
四位中,有三位是長安纓世族的后裔,還有一位是大儒簡文清的獨,四位年齡從二十到四十不等,全都是立志終不嫁的大才。
傳旨的宮人又說,學生們必須在家準備好行裝和筆墨,開學那日,將由禮部尚書及書院兩位院長主持鼓篋之禮(注1),行禮過后,學生們還需當場繳納束脩,當然,這束脩的定額僅是每人三匹絹,幾乎只是象征地收個費。
旨意一傳到滕府,滿府的人都忙碌起來。
此前程伯就將書院一應事項都打聽好了,知道書院管理嚴格,娘子學后一月才能回來一次,唯恐小主人在書院里過得不順意,便親自跑到潭上月來指揮春絨等人準備行裝。
這一整日,潭上月喧鬧不已,下人們進進出出,忙著打點滕玉意的箱篋。
滕玉意自己也沒閑著,跑到廚司讓廚娘把模拿出來,凈了手親自面團。進了書院這鮮花糕就做不了,趁今日做好了,正好趕在開學之前送到青云觀去。
小主人一上手,廚司里的人自是毫不敢慢怠,不是幫著遞石,就是幫著剪花瓣。驪山上帶下來的玫瑰花瓣遠不夠用,一大半花朵是碧螺帶著小丫鬟們在府里臨時剪的。
滕玉意先用玫瑰子將面團淡,再將花瓣與石調在一起,同時在餡料里摻甜的果脯,末了嘗了嘗餡料,絕勝和棄智跟一樣吃甜的,藺承佑卻喜歡清淡的,所以一份餡料甜一些,另一份餡料淡些。
隨后細細把面團一朵一朵玫瑰花的形狀。
Advertisement
這是極為細的活計,一做就做到了下午,最終做出八屜子面團,每一朵都惟妙惟肖,滕玉意左看右看,自己覺非常滿意,興致讓廚娘們把面團收到廚架上,明早再上屜蒸。
第二日這點心還沒送走,青云觀的帖子就送來了。
帖子是絕圣和棄智寫的,說他們有要事要同滕玉意商量,請滕玉意即刻到東市的明月樓一敘。
程伯有些費解:“明月樓是一家專做江南菜的菜館,歷來只款待豪紳巨賈,菜價可謂不菲,兩位小道長這是——”
言下之意,以絕圣和棄智的做派,絕不可能約滕玉意在那種地方見面。
滕玉意百無聊賴用小銀匙舀著碗里的酪鮮櫻,這帖子哪是絕圣棄智寫的,絕對是出自藺承佑之手,想來那厲鬼有著落了,便慢條斯理道:“小道長摳門歸摳門,待人卻很周到,難得約我這樣的好朋友出門,就不能大方一次嘛,事不宜遲,幫我備馬吧。”
程伯仍有些疑的樣子,滕玉意卻忙著讓春絨找出男子的錦袍和幞頭,一番裝束后,又讓端福去易容。
待到主仆都換了相貌,就將那幾盒鮮花糕給端福捧著,一行人大搖大擺去了東市。
到了明月樓門口,一就知道程伯為何不信絕圣和棄智會選在此面了,因為這酒樓實在是貴盛至極,是樓面窗屜上的銀鏤朱漆就比別家考究不。
奇怪偌大一座酒樓,門外幾乎沒客人,滕玉意店打聽小道士,店家像是等候多時了,竟親自迎出來道:“是王公子吧?快隨小人上樓。”
然而到了二樓雅室,卻沒看到絕圣和棄智的影子。
店家熱絡地端茶送點心:“王公子在此稍等,兩位小道長還在路上。”
Advertisement
滕玉意只好先坐下了。
***
藺承佑在大理寺忙。
那日大寺和各家道觀接到尺廓出現的消息,立刻在城中四巡邏,巡視一番并未發現尺廓的跡象,看來尺廓還未潛城中,礙于此來去無蹤,眾僧道仍連夜在城外設置陣眼,清虛子一從山上下來,就趕到城外親自坐鎮指揮此事。
相比僧道們的忙碌,大理寺這幾日卻極為清閑。
不知是不是巧合,自打皓月散人伏法,各州縣已經好些日子沒呈送案子來了,同僚們手里只有一些往日積的案子,嚴司直和藺承佑這等一貫辦案利索的,手頭就更清閑了。
從驪山下來這晚,藺承佑先是幫著師公布陣,次日一早又讓絕圣和棄智給滕玉意發帖子,看看天還早,想想手頭那幾樁案子還有不疑點,就縱馬到了大理寺。
每回嚴司直都到得最早,今日也不例外,藺承佑進辦事閣時,嚴司直端端正正坐在軒窗前,正忙著整理幾樁舊案的案呈。
藺承佑對嚴司直的勤勉早就見怪不怪了,笑道:“嚴大哥。”
嚴司直擱下筆:“來的正好,我有事要同藺評事商量。”
說著把自己寫的一沓錄簿推到藺承佑面前:“早上整理這幾樁案子,別的都好說,唯獨胡季真一案,卻是連案呈都不知怎樣寫。案發至今,沒有目擊證人,沒有兇,沒有清晰的害人機,甚至都沒能從害人口里聽到只言片語,現在胡季真面上與痰迷心竅癥一模一樣,僅憑這個就懷疑盧兆安與此事有關,未免證據不足,可想要查到更多的證據,整件事面上全無痕跡,簡直無下手。”
藺承佑坐下翻了翻錄簿,這上頭的每條記錄他都很,前些日子他為了查盧兆安調派了不人手,結果因為皓月散人一案又中途擱置了,這幾日一閑,他和嚴司直就重新著手調查此案了。
Advertisement
“既然有那麼多模糊不清之,不如先從明朗之手。”藺承佑點了點錄簿上的某一,“行兇手法——明。胡季真是被人掉了一魂一魄才變現在這樣的,這是一種取魂的邪。”
嚴司直點了點頭,依照藺承佑的思路寫下第一行。
藺承佑又道:“行兇時辰——明。胡季真是上月的二十出的事,確切地說,是他同好友們從慈恩寺回來后被害的。當日他未時末與最后一位友人分手,回到胡府已是申時末,而且一回府就發了病,所以兇手只能是在未時末——申時末這兩個時辰之的手。”
嚴司直再次頷首。
“行兇地點——明。”藺承佑說,“胡季真是在醴泉坊的得善大街與友人們分的手,那地方離胡府所在的義寧坊只隔一條街。胡季真僅被人掉了魂一魄,最初的半個時辰面上看不出端倪,兇手應是一直跟在胡季真的后頭,所以能控胡季真騎馬回家,但行兇的地點不會離胡府太遠,因為若是拖得太久,胡季真會出越多端倪,由此可見,行兇之就在醴泉坊的得善大街與義寧坊附近,甚至就在半個時辰的腳程。”
嚴司直寫下第三條。
頓了頓,他凝眉道:“那……最關鍵的行兇機呢?胡季真在國子監念書,今年才十四歲,雖耿直,心腸卻很,聽說平日連府里下人都舍不得斥責,他父親胡定保在兵部任侍郎一職,也是外圓方之人。要說盧兆安有加害胡季真的機……是,尸邪闖王府那一晚,盧兆安是只顧自己逃命把胡季真關到門外,但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即使胡季真到宣揚,盧兆安也可以說這是胡季真的一面之詞,僅憑這一點就害人,會不會風險太大,而且我們至今沒發現盧兆安會邪的蛛馬跡。”
藺承佑出底下的一份記錄:“加上這個是不是就清楚一點了?胡季真的同窗好友杜紹棠那日去胡府探,結果胡季真似是被好友關心自己的舉發了記憶,驚之下居然吐出了一句話:‘別過來,我什麼也沒瞧見’。那句話是他犯病以來唯一一句口齒清楚的話,如果不是胡言妄語,那麼很可能是他被害前最強烈的一個念頭。”
嚴司直著那一:“難不胡季真是因為不小心撞破了什麼才被害?這樣說來,機倒是稍稍明朗些了。”
藺承佑:“這些年邪一黨為了躲避朝廷的追查,甚用取魂害人,那日用這法子對付胡季真,想來也是迫不得已。直接殺死胡季真,必定會驚大理寺和朝廷,用這種取魂害人就穩妥多了,害人面上與痰迷心竅癥差不多,就連尋常的僧道也休想看出不妥,要不是胡定保病急投醫央我上門探視,誰也不會知道胡季真是被人蓄意謀害的。”
嚴司直思索:“可那日胡季真都快走到家門口了,又能撞見什麼要命的把柄?當時并未天黑,坊街上到是人。”
藺承佑靜靜琢磨了下,隨手找了一卷竹簡在上頭勾畫:“從他驅馬走到得善大街來看,他是打算直接回家的,但不知為何又臨時改了主意,附近并無店肆,也不大像要臨時去買東西,平日像這種況,一般都是——”
嚴司直一愣:“半路撞見了人?或是被什麼人攔住了?”
藺承佑想了想:“無故被人攔路,胡季真必定不肯下馬,雙方一起爭執,不了引起旁人的注意,可當日這兩個路口沒人起過爭端,查問附近的酒肆,也證明胡季真當日并未與人進店喝過酒,所以很有可能是某個人或是某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胡季真或是悄悄驅馬跟隨那人,或是被那人邀請到自己家中,再然后,胡季真就撞見了一些不該見到的東西,并因此被害。”
嚴司直著桌上的竹簡,藺承佑在上頭畫了代表胡季真和座騎的一人一馬,以及這一人一馬走過的路段。
藺承佑接著在那個小人的西北角和東北角各畫了一宅子,一是普寧坊,一是修祥坊。
他先指了指普寧坊:“盧兆安現今就住在普寧坊,恰好就在得善大街的西北角。”
又指了指東北角的修祥坊:“那日他又在修祥坊的英國公府赴宴,巧也不遠,他如果借故從席上出來,是有可能與胡季真相遇的。”
猜你喜歡
-
完結239 章
休夫
挺著六月的身孕盼來回家的丈夫,卻沒想到,丈夫竟然帶著野女人以及野女人肚子裡的野種一起回來了!「這是海棠,我想收她為妾,給她一個名分。」顧靖風手牽著野女人海棠,對著挺著大肚的沈輕舞淺聲開口。話音一落,吃了沈輕舞兩個巴掌,以及一頓的怒罵的顧靖風大怒,厲聲道「沈輕舞,你別太過分,當真以為我不敢休了你。」「好啊,現在就寫休書,我讓大夫開落胎葯。現在不是你要休妻,而是我沈輕舞,要休夫!」
65.8萬字8 77347 -
完結46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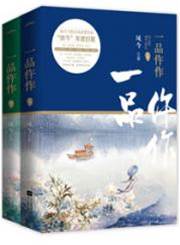
一品仵作
這是一個法醫學家兼微表情心理學家,在為父報仇、尋找真兇的道路上,最後找到了真愛的故事。聽起來有點簡單,但其實有點曲折。好吧,還是看正經簡介吧開棺驗屍、查內情、慰亡靈、讓死人開口說話——這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乾了。西北從軍、救主帥、殺敵首、翻朝堂、覆盛京、傾權謀——這不是仵作該乾的事。暮青也乾了。但是,她覺得,這些都不是她想乾的。她這輩子最想乾的事,是剖活人。剖一剖世間欺她負她的小人。剖一剖嘴皮子一張就想翻覆公理的貴人大佬。剖一剖禦座之上的千麵帝君,步惜歡。可是,她剖得了死人,剖得了活人,剖得了這鐵血王朝,卻如何剖解此生真情?待山河裂,烽煙起,她一襲烈衣捲入千軍萬馬,“我求一生完整的感情,不欺,不棄。欺我者,我永棄!”風雷動,四海驚,天下傾,屬於她一生的傳奇,此刻,開啟——【懸疑版簡介】大興元隆年間,帝君昏聵,五胡犯邊。暮青南下汴河,尋殺父元兇,選行宮男妃,刺大興帝君!男妃行事成迷,帝君身手奇詭,殺父元兇究竟何人?行軍途中內奸暗藏,大漠地宮機關深詭,議和使節半路身亡,盛京驚現真假勒丹王……是誰以天下為局譜一手亂世的棋,是誰以刀刃為弦奏一首盛世的曲?自邊關至盛京,自民間至朝堂,且看一出撲朔迷離的大戲,且聽一曲女仵作的盛世傳奇。
203萬字8 29155 -
完結977 章

嫡女醫妃權傾天下
她是簪纓世家的嫡長女,生而尊貴,國色天香,姿容絕世; 上一世,她傾盡所有,助他奪得天下,卻換來滿門抄斬; 上一世,害她的人登臨鳳位,母儀天下,榮寵富貴,而她被囚冷宮,受盡凌辱; 重生于幼學之年,她再也不是任人擺布的棋子,一身醫術冠絕天下,一顆玲瓏心運籌帷幄,謀算江山; 這一世,她要守護至親,有仇報仇,有怨報怨; 這一世,她要讓那個縱馬輕歌的少年,無論刀光劍影,都長壽平安!
177.9萬字8 62454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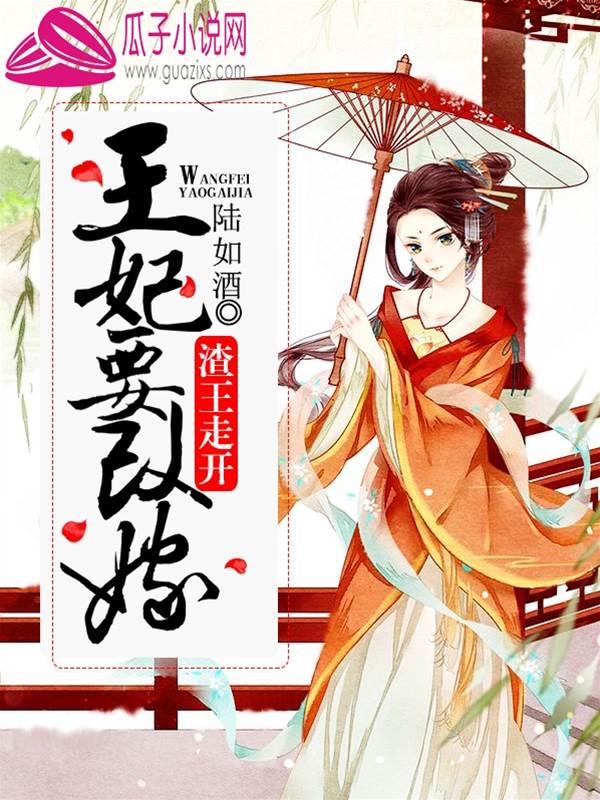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86 章

東宮嬌藏
裴幼宜是齊國公獨女,憑著一副好樣貌和家中的背景,在汴京城中橫行霸道。京城的貴女,個個視都她為眼中釘肉中刺。直到這天,齊國公犯錯下了獄,裴幼宜也跟著受了牽連,正當她等候發落之際,宮中傳出消息,她成了給太子擋災之人。擋災這事說來滑稽,加上國公爺被冷落,連帶著她在宮裏的日子也也不好過同住東宮的太子趙恂惜字如金,性格冷漠,實在是個不好相處的人。好在二大王趙恒脾氣秉性與她相當,二人很快就打成一片。衆人皆以為,裴幼宜以如此身份進了東宮,日子應該不會好過。結果裴幼宜大鬧宮中學堂,氣焰比起之前更加囂張。衆人又以為,她這樣鬧下去,過不了多久就會被太子厭煩,誰知……裴幼宜每每掀起風波,都是太子親自出手平息事端。擋著擋著,太子成了皇上,裴幼宜搖身一變成了皇後。-------------------------------------趙恂從宗學領回裴幼宜,今日犯的錯,是與慶國公府的**扭打在一起。裴幼宜眼圈通紅,哭的三分真七分假,眼淚順著腮邊滑落,伸出小手,手背上面有一道輕不可見的紅痕。太子皺眉看了一陣,次日便親臨慶國公府。第二日慶國公**頂著衆人錯愕的目光給裴幼宜道歉,裴幼宜不知她為何突然轉了性子,以為是自己打服了她,于是揚起小臉眼中滿是驕傲。遠處趙恂看見此情景,無奈的搖了搖頭,但眼裏卻滿是寵溺。閱前提示:1.雙C,1V1,微養成2.架空仿宋,務考究。4.年齡差5歲。5.尊重每一位讀者的喜好,不愛也別傷害。內容標簽: 勵志人生 甜文搜索關鍵字:主角:趙恂,裴幼宜 ┃ 配角:很多人 ┃ 其它:
27.9萬字8 1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