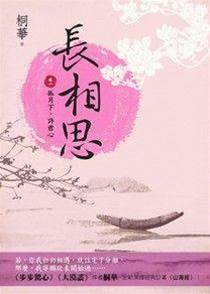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國醫狂妃︰邪王霸寵腹黑妃》 第41章 王妃爬牆(一)
尼瑪——
丫鬟也是爹媽生的,丫鬟也是人!
素暖氣急敗壞掄起拳頭就朝錦王那張顛倒眾生的俊臉揮舞過去。錦王眼疾手快,握著纖細雪白的手腕,“你竟敢對本王不敬?”
不敬又怎樣了?像你這種高高在上輕賤人命的人渣,難道不該教訓嗎?素暖又揮起另一個拳頭,然而依然不偏不倚的被錦王截住。
男人的力氣大如蠻牛一般,素暖的雙手毫不能彈。
好吧,手不能,就用腳——
看我的掃堂——
臥槽,的太短,錦王的大長往後,隻能掃起一片塵灰。
錦王娟狂邪肆一笑。這讓素暖決定自己就跟個跳梁小醜一般,心裡登時覺得挫敗。
憤懣的瞪著麵前嘚瑟非凡的男人,手不能打,腳不能踢,媽的,不是還有嗎?
忽然俯,一口向錦王的手背咬去……
是真的很用力了。可是對方竟然冇反應?難道不該嗷嗷大嗎?
Advertisement
那就再用力……
咦,對方的神經係統莫非麻痹了?
素暖著兩排牙齒印,滲出,哦,好像咬得太重了?
可是這傢夥怎麼不出聲?
十分無辜的著錦王,他看到眼裡那抹不易察覺的歉意,的薄扯出一抹飛揚的弧度。這點痛,對他一個大男人來說算的了什麼?
素暖用袖,將他手背上的跡給了。
錦王的眼底,泄出一抹溫煦的目。
忽然,將打橫抱起來,不顧周遭侍衛驚詫的目。徑直朝添香院走去。
素暖那一刻,心忽然張得跳起來。
這個男人要乾嘛?
將放在溫舒適的錦床上,著驚若寒蟬的可模樣,溫潤如玉的大手,將淩的髮整理到耳後。
素暖直愣愣的著他,整個子僵如雕。
就擔心,這個男人會忽然不擇食的將生吞活剝了,畢竟他們是夫妻。他有這個權利。
Advertisement
錦王的目及到瑟的模樣,不悅,這分明是對自己有芥的。看得出來,有意識的在逃避自己的解近。
想到很可能——不是真傻。
他心裡忽然湧起酸酸的覺,讓他的緒十分低落。
他淡淡然瞥了一眼,轉大踏步離去。
素暖舒了口氣。
外麵的天,已經完全黯黑了下來。
素暖對輕舞的擔心,更加劇烈。
是鐵了心要逃出錦王府的。
既然大門不能走,那就另辟蹊徑。
院牆……要爬牆走人。
趁黑,簡單收拾了一下包袱,重點是拿走金銀珠寶,畢竟出門在外,冇有銀子可是萬萬不能的。然後,夜深人靜時,素暖拉開了大門。
本是月黑風高夜,卻被錦王府的火把照的燈火通明。前門。後門,臥槽,連狗也有人守著。素暖咬咬牙,錦王府的院牆有三米高吧?摔下去應該死不了。
Advertisement
了手裡的包袱,素暖悉悉索索的往黑的地方索著,侍衛不時的巡邏著,給前行帶來阻礙。有侍衛來的時候。就趴在灌木叢中,一點點爬著,好在年時有野戰經驗,雖然辛苦,為了輕舞,也值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74 章

姑娘今生不行善
盛京人人都說沛國公府的薑莞被三殿下退婚之後變了個人,從前冠絕京華的閨秀典範突然成了人人談之變色的小惡女,偏在二殿下面前扭捏作態,嬌羞緊張。 盛京百姓:懂了,故意氣三殿下的。
94.2萬字8 13581 -
完結369 章

權臣心上撒個嬌
蕭懷瑾心狠手辣、城府極深,天下不過是他的掌中玩物。 這般矜貴驕傲之人,偏偏向阮家孤女服了軟,心甘情願做她的小尾巴。 「願以良田千畝,紅妝十里,聘姑娘為妻」 ——阮雲棠知道,蕭懷瑾日後會權傾朝野,名留千古,也會一杯毒酒,送她歸西。 意外穿書的她只想茍且偷生,他卻把她逼到牆角,紅了眼,亂了分寸。 她不得已,說出結局:「蕭懷瑾,我們在一起會不得善終」 「不得善終?太遲了! 你亂了我的心,碧落黃泉,別想分離」
65.4萬字8.18 6732 -
完結5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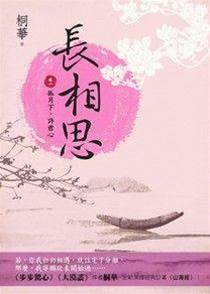
長相思
生命是一場又一場的相遇和別離,是一次又一次的遺忘和開始,可總有些事,一旦發生,就留下印跡;總有個人,一旦來過,就無法忘記。這一場清水鎮的相遇改變了所有人的命運,
63.4萬字8 5857 -
完結790 章

重生后我被繼兄逼著生崽崽
上輩子的謝苒拼了命都要嫁的榮國候世子,成親不過兩年便與她的堂姐謝芊睡到一起,逼著她同意娶了謝芊為平妻,病入膏肓臨死前,謝芊那得意的面龐讓她恨之入骨。一朝重生回到嫁人前,正是榮國侯府來謝家退婚的時候,想到前世臨死前的慘狀,這一世謝苒決定反其道而行。不是要退婚?那便退,榮國侯府誰愛嫁誰嫁去!她的首要任務是將自己孀居多年的母親徐氏先嫁出去,后爹如今雖只是個舉人,可在前世他最終卻成了侯爺。遠離謝家這個虎狼窩后,謝苒本想安穩度日,誰知那繼兄的眼神看她越來越不對勁? ...
106.2萬字8.18 218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