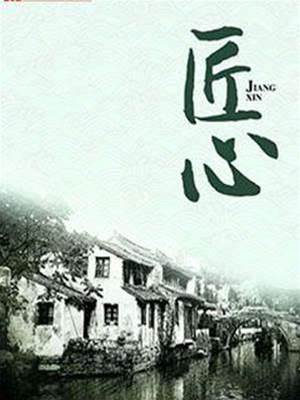《太陽雨》第2章
到襲擊的野做出的第一反應永遠是回擊,傅宣燎也不例外。
與皮糾纏的牙齒還沒松開,他就強行出了自己的胳膊,反手準地掐住面前人的脖子,猛一使勁,將襲擊者推到對面墻上。
踉蹌兩步,劇烈的撞擊出間一聲悶哼,竄鼻腔的鐵銹味令視線花白了一瞬,待猛吸一口氣,眼前的面容逐漸清晰,時濛才慢慢卸了力氣。
手背牽起的疼痛令傅宣燎面目猙獰,察覺時濛放松,他又覺得好笑:“真以為我不敢你?”
走廊進一點燈,傅宣燎背站著,深邃五在臉上裁出連片影,時濛瞇著眼睛凝他,在愈漸稀薄的息中,將貪癡迷藏在黑暗里。
一方放棄掙扎,角斗便失去意義。傅宣燎松開五指,背過去迎著抬起手看傷,低聲咒罵了句什麼。
去樓下問阿姨拿藥箱的時候,到披浴袍端著紅酒杯從樓上下來的時思卉。找了個空位坐下,瞧了一眼傅宣燎手上的傷,笑說:“都出了,要不要打個破傷風?”
傅宣燎沒理會,清洗完傷口了碘酒,轉就要上樓。
時思卉的聲音在后響起:“要是我弟弟還在,何至于……”
后面的話在嚨里,傅宣燎也不想聽,抬腳拾級而上。
許是喝多了,時思卉有些口無遮攔,起追問:“你就這麼認了嗎?你忘了時沐,忘了答應過他的事了嗎?”
腳步一頓,傅宣燎沒有轉頭。
“你們都忘了。”他平靜地說,“我還記著那些做什麼?”
時濛畏寒,冬日里總是將房間里的暖氣調得很高。
進屋甩上門,傅宣燎把下的大丟在床上,環視一圈,沒人,應該在洗澡。
Advertisement
這間二樓最里側的房間是個套房,臥室、小型客廳加上衛生間,功能齊全,原本是時家老爺子留給最寵的兒子的臥房,幾年前被搶了來,了時濛發瘋的地方。
回頭品了品“搶”這個字,傅宣燎開雙背靠沙發,勾譏誚一笑。
可不就是搶麼,時沐有的他都要有,無論死活,統統先搶來再說。
衛生間隔音很好,時濛洗完出來的時候,看見歪在沙發閉目養神的傅宣燎,先是一愣,像是沒想到他會這麼快回來,接著視線向下,掃過他搭在膝蓋上的手,不過兩秒又移了開去,徑自走向臺。
傅宣燎睜開眼時,目的便是裹在沉沉夜中的頎長影。
與開著空調蓋棉被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是,時濛喜歡在暖氣充足的房間里打開窗戶看夜景。
不算溫的風起浴袍空的袖管,現出常拿畫筆的纖長手指,拂過耳畔漉漉的發尾,出綴滿水珠的白皙脖頸,其中約能見幾枚突兀指印,如散落雪地的點點猩紅。
不得不承認,是一幅極其人的畫面。
于是傅宣燎站起,步上前,長臂攔過細韌腰肢,兩人摔進床鋪里滾一圈。
借著姿勢先埋首進尚余水汽的頸窩,將未的齒沿著紅痕魯啃咬,傅宣燎忽地仰起頭,居高臨下地問:“疼嗎?”
本意想讓時濛服,誰想他坦然地承認了:“疼啊。”
弄得傅宣燎沒好氣,擒住時濛肩膀的手不控地用了點力氣:“那還咬?”
下的人瞇著眼,仿佛痛于他來說也是。
“不過……”時濛上來,蒸騰熱氣黏住沙啞嗓音,“我會讓你更疼。”
這一晚,分不清誰贏誰輸。
次日醒來,傅宣燎瞧著鏡子里昨天還算得上完好的又添了幾塊青紫,扯了下角,又被邊的痛弄得皺眉,表不可謂不糟糕。
Advertisement
拿起外套穿上的時候,偶然瞥見搭在沙發扶手上的白襯衫,傅宣燎不舍放棄挑釁的機會,扭問時濛:“哪兒弄來的?”
剛睡醒的時濛陷在凌被子里,聞言輕飄飄瞥一眼。
傅宣燎拎了那襯衫丟到床上:“昨天沒看仔細,穿上我瞧瞧。”
半張臉被蓋住,被窩里出一截藕白手臂,隨手掀開襯衫,時濛翻了個,用屁對著搗的人。
想到昨晚這人在自己下輾轉的模樣,傅宣燎走到床邊,單手撐在時濛側傾下,著他薄薄一層耳廓,皮笑不笑地說:“你不穿,我怎麼知道是青出于藍,還是東施效顰啊?”
十月的第四個星期天上午,時濛起床后先撕掉用紅筆圈上的星期六那張日歷,然后拿出工剪刀,把只穿了一次的襯衫剪得稀碎。
頂層閣樓冬冷夏熱,家里沒人愿意上去,時濛問父親要來布置了畫室。
上個月完的那副薄涂畫已經干,指腹輕輕拂過畫布上的斑斕塊,時濛顛簸的心緒終于安定下來。
他將畫布從畫架上摘下,卷一束塞進后的背包里。
出門下樓的時候到從二樓房里出來的時思卉,經過一天休憩,束起頭發戴上眼鏡,又恢復了職場英的干練打扮。
看見時濛后的畫,時思卉問:“去孫老師那兒?”
時濛走在前面,悶悶地“嗯”了一聲。
“他就是個帶藝考生的。”時思略帶譏諷地,“你不都能靠賣畫賺錢了嗎?還要跟他學?”
“……嗯。”
兩人同時下樓,一齊走到外面,灑在上的時候,時濛角和脖子上的痕跡暴無。
翻涌而上的憤恨不甘被強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輕蔑和譏誚。瞧著時濛那過分致的側,時思卉說:“你母親也住在那附近吧?”
Advertisement
時濛手拉開車門,聞言偏頭看去,神些許迷茫。
“勾三搭四的病難改得很,尤其是當第三者,橫刀奪什麼的。”說著別人的事,時思卉的目卻盯著時濛,“你可得看好,別再讓我們時家跟著丟臉。”
路上等紅燈的時候,車窗外的路邊有個小孩走路摔了跟頭,被母親模樣的人抱在懷里哄。
如果說疼了會哭是天,那麼疼多了學會沉默便是天分了。時濛看見那孩子還是哇哇哭個不停,神如死水般漠然,甚至覺得很吵。
孫老師家住城東,老小區多層的一樓。時濛把車停在北面圍墻下,走進鐵門半掩的院子前,先把領口往上拉了拉,然后越過朝西的門,徑直爬臺階進了主屋。
上了年紀人的住一樓總沒有關門的習慣,何況隔壁就是自家繪畫班。孫雁風正往食盆里倒貓糧,就聽自家貓“喵”了一聲,從斗柜上跳下去,扭著屁走到門口。
“濛濛來了。”看清來人,孫雁風招手道,“站著干嗎,快進來坐。”
時濛在桌邊最靠外面的椅子上坐下,皮油水的橘貓在桌下圍著他的蹭來蹭去,他不聲地收了收。
“它倒是黏你。”孫雁風端著茶壺回到客廳,給時濛斟上一杯,“平日家里一來人就躲沒影,看來它跟你有特別的緣分。”
接過熱茶捧在手心,時濛才得空點余看下頭的貓,那貓剛好也仰起腦袋看他,四顧無言,目不轉睛,仿佛坐實了“緣分”二字。
習慣了徒的寡言,孫雁風轉去搬畫架,像每個上了年紀的老頭那樣邊做事邊說閑話:“你媽媽最近也養了只貓,撿的,黑白花,木木,木頭的木,你要是哪天得空啊……”
布完畫架轉,看見時濛已經將帶來的畫布鋪在桌上,用刷子上油了,看樣子是一個字也沒聽進去。
孫雁風嘆了口氣,在邊上看了會兒,負手回屋去了。
隔壁就是繪畫班,工作日孫雁風在學校教室帶藝考生,周末在家授課,星期天上午學生最多。
因而時濛擁有了半日寧靜,給畫作仔細刷了油,裱了窄邊木框,一忙就是三個多小時。
中途有一段曲,找螺刀的時候拉開斗柜的屜,發現里頭卷著的幾幅畫,其中一副散開了出標有署名的一角,清秀的“沐”字令時濛想起了早上傅宣燎口中的“東施效顰”。
時濛微張的抖了幾下,手掌握又松開,到底念及不是自己的東西,強行收斂了破壞的。
不到中午,時濛便要走了。
留他自是留不住,孫雁風忙洗了手從教室出來:“畫還是老樣子,我看況幫你賣了?”
時濛點點頭,說:“謝謝老師。”
不想讓人空手回去,孫雁風了斗柜上的一條煙往時濛包里揣:“老朋友送的,都不知道我肺不好,勁兒小的也不得了……”
背包拉鏈被拉嚴,時濛沒讓東西進包里。
“我也不了。”他說著,把空癟癟的包甩到肩上。
孫雁風霎時一怔,把人送出門才想起來問:“怎麼不了?”
印象中時濛剛學會煙不過半年,正是癮大的時候,上個月來這里時口袋里還揣著包士煙。而且這孩子固執得很,長輩的勸導一概不會聽,能讓他做出改變的只有他自己的命令。
然而時濛并不想解,只丟下一句“戒了”,繼續往外走。
“你媽媽最近不好。”孫雁風跟了上去,像是怕沒機會說,“很想你,有空的話,去看看吧。”
從一個長輩口中說出這種類似請求的話,時濛卻毫沒有容的跡象。
正午日頭高懸,他抬頭天,太散開的暈一圈連著一圈,仿佛無窮無盡,照著他蒼白無的臉,頭暈目眩。
又是傍晚,時濛做了個夢。
漆黑的,只有聲音,零碎的聲音,碗碟砸下的刺耳,桌椅倒地的轟鳴,雷聲,雨聲,在沒有的暗角落里,如同霉菌瘋狂滋生。
他聽見母親歇斯底里的哭喊,同伴言無忌的嘲笑,畫紙被撕碎的聲音飄在很遠的地方。
“我時沐,是你的哥哥。”稚的音。
“在這個家里,你必須擺正自己的位置。”威嚴的男人。
“救救他,救救他吧,媽媽求你了。”尖銳的聲。
“為什麼死的不是你?”帶著哭腔的指責。
“你以為進了這個家門,就是時家的人了?”事不關己的提醒。
“等著吧,你會遭報應,你們都會遭報應的。”鋪天蓋地的詛咒。
……
時濛在夢中捂住耳朵,在椅子上蜷,驚醒時甚至分不清自己何地。
緩慢地出手,落在窗外一片朦朧黑暗里,神智回復清明的同時,時濛想起今天是最討厭的星期天,懨懨地再度合上眼。
又要等上六天,等到下個星期六……
“醒了?”一道低沉嗓音自后傳來,打斷了時濛的思緒。
先是肩膀一,待到反應過來是誰在房間里,時濛幾乎是立刻扭過去,赤腳踩地站起。
夢里最后的聲音來自一個男孩,與所有人都不一樣,他說:“你畫得真好看。”
還說:“別怕,這里沒有人會欺負你。”
為了守住這方安全的領地,時濛不管不顧地撲了上去,把人抱在懷里的時候,倉皇的心跳才重歸平靜。
耳邊響起一聲低笑,被抱住的人在很近的地方開口:“看到我這麼高興?”
時濛不說話,也不。
似是覺得他的反應有趣,傅宣燎又笑了一聲:“你的鞋呢?”
不想聽下去,時濛故技重施,后仰,封住他說話的。
這一吻相比昨天多了溫,了蠻橫,也許因為昨天了傷,不得不收斂。
還因為今天是星期天,多一點都算來的。
克制與放肆既矛盾又和諧,齒纏繞的尾聲,傅宣燎低頭,看見時濛攀上他腰的兩條,忍不住嗤道:“你還真是不客氣。”
細瘦腳踝在后腰叉,的腳背隨著呼吸晃起伏。時濛將雙手環在傅宣燎脖子上,后背著冰冷白墻,眼底卻被有溫度的填滿。
對視的剎那,傅宣燎愣了一下,神幾分詫異幾分郁,轉瞬又變回混不吝的笑。
溫熱吐息噴在頸側,傅宣燎湊近,半真半假地問:“時濛,你不會真的喜歡我吧?”
很久以前聽說,得到雙方當事人認可的記憶才稱得上一段真實的故事,而被一方忘掉的,最多只能算一場嘩眾取寵的獨角戲。
此刻的時濛忽然想起正午見過的太,灼燙,刺眼,卻還是讓人想要靠近。
于是他選擇閉上眼,收臂膀,再疼也緘默不語。
猜你喜歡
-
完結6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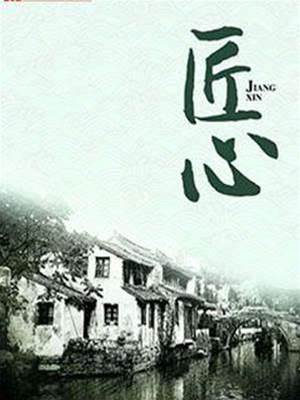
匠心
陸商在酒吧談事的時候,順手救回來一名臟兮兮的少年,本是順手之舉,不料他看見了這名少年背后的槍傷,十年前的記憶浮上腦海。 陸商問他:“你叫什麼?” “小黎……我姓黎,他們都叫我小黎。” “沒有名字嗎?” “不記得了。” 陸商說:“就叫黎邃吧,你以后跟著我。” 從那天起,陸商身邊多了一位叫黎邃的小情人。 許多年后,梁醫生嘲笑他,別人的心沒要著,還把自己的心搭進去了,陸老板,這買賣不劃算啊。 陸商望著在廚房做飯的英俊青年郁悶地想,明明撿回來的時候還是只字都認不全的小烏龜,怎麼一眨眼就變成了見他就撲倒的大狼狗了呢? 【設定】成長型忠犬攻×心臟病精英受 【屬性】現代架空都市,年下,一點養成,狗血慢熱,1V1,HE,甜虐。
24.5萬字8 3384 -
完結102 章

取向阻擊(ABO)
賀天看著指尖的煙快燃完了,冒著縷縷白氣。 他隨手抖了抖灰,把煙頭隨意摁到紅毛的肩膀上,“別裝了,知道你很抗打。” 經常穿的運動服外套被煙頭給燙出個黑洞來,紅毛緩緩地抬起頭,因為挨揍而充血的眼睛死死地瞪著賀天,“操你媽。”
4.7萬字8 3307 -
完結161 章
契子
在遙遠的天宿星,生活著這樣一群特殊的智慧生命,他們沒有幼年,也沒有老年,沒有出生,也沒有真正的死亡。他們以一種極特殊的方式降臨世間,在一代代的輪回中保留下了關於生存最原始的記憶,他們就是天宿人。 每一個天宿人在找到心儀的對象後,若要與對方結為伴侶,就必須經歷一場生死角逐的成人儀式,儀式上的勝出者,將成為配偶關系中絕對的支配者。 而落拜的那一方,則被稱為——契子。
51.8萬字8 1189 -
完結44 章
茍茍
此作品列為限制級,未滿18歲之讀者不得閱讀。 惡趣味表裡不一鬼畜腹黑攻x後期女裝雙性美人受 三觀不正 囚禁 雙性女裝 生子 攻略微鬼畜 靦腆弱受 一切為了肉
6.9萬字8 31338 -
連載116 章
精打細算
就算幸福只剩一把骨灰,我都不會放手。 事關愛情、還有銀行職員的各種悲慘 CP:窮小子清冷攻別扭純情受,一往情深的好文一篇。
34.3萬字8 43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